[意]内洛·波嫩特 | 《艺术批评史》1964年意大利文版前言
廖内洛·文杜里[Lionello Venturi,1885—1961]一生勤奋且著述甚丰,其《艺术批评史》[Storia della critica d’arte]仍然是最为重要,并应当作为对于准确解读其批评思想不可或缺的著作。此外,早在此书撰写及1936年英文版面世之时,这部著作对作者的方法论取向来说便是决定性的转折点;这一转向极大地有助于他克服某些方法论上的自相矛盾,那些矛盾彼时依旧存在于他的思想上,亦即其理想主义类型的理论教育与经检验公认的、有效的纯粹可视性诸方法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这种方法论上的微调让早对现代艺术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文杜里,赋予这些问题有机的整理与分类,并且坚称它们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性。而且绝非毫无意义的是,廖内洛·文杜里于《艺术批评史》出版的同时,还在法国出版了另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即包括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的油画、素描与版画的分类图录[catalogo ragionato=Cézanne,son art,son oeuvre,Paris:P.Rosenberg,1936],他在图录卷首所写的评论文章,包括对这位艺术家在艺术上所受褒扬与贬损的考察,使得这部分类图录至今仍然是所有解读这位普罗旺斯艾克斯地区[Aix-en-Provence]的大师全部作品的必要基点。
《艺术批评史》已有几种不同语种的版本问世,最初是英文版于1936年在美国刊印(History of Art Criticism,New York:E. P. Dutton and Co.)(图1),之后法文版于1938年发行(Histoire de la critique d’art,Brussels:Editions de la Connaissance)(图2)。其意大利文版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付梓,作者扩充了最后一章[英文初版没有的Cap. XI—La critica sull’arte del secolo XX(第11章——关于20世纪艺术的批评)]并对之稍作修改,由佛罗伦萨[Firenze]的Edizioni U出版社辑入“正义与自由”[Giusezza e Libertà]丛书并先后有1945年与1948年两版(图3)。廖内洛·文杜里于1961年8月14日卒于罗马,他在临终的前几天便已开始整理其为此书新版收集的资料。他打算在新版最后一章里讨论与当代艺术情形有关的批评家与理论家,从立体主义[cubismo]起,从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到活跃在法国的德国画家和摄影师沃尔斯[Wols=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1913—1951]与波洛克[Paul Jackson Pollock,1912—1956]。再有,他发表在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手册第4期》[Quaderno n.4](1951)上的演讲稿《现代艺术的理论前提》[Premesse teoriche dell’arte moderna](收录在1956年罗马Bocca出版社出版的《评论文集》[Saggi di critica]),已提出修订版里应有的思路。而且,廖内洛·文杜里于1955年达到年限,辞去罗马大学[Università di Roma]现代艺术史教席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作为非长聘教授,在该校研究生院所讲授的,恰好也是有关当代艺术批评史的系列课程。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仍然只能以笔记与注解的形式保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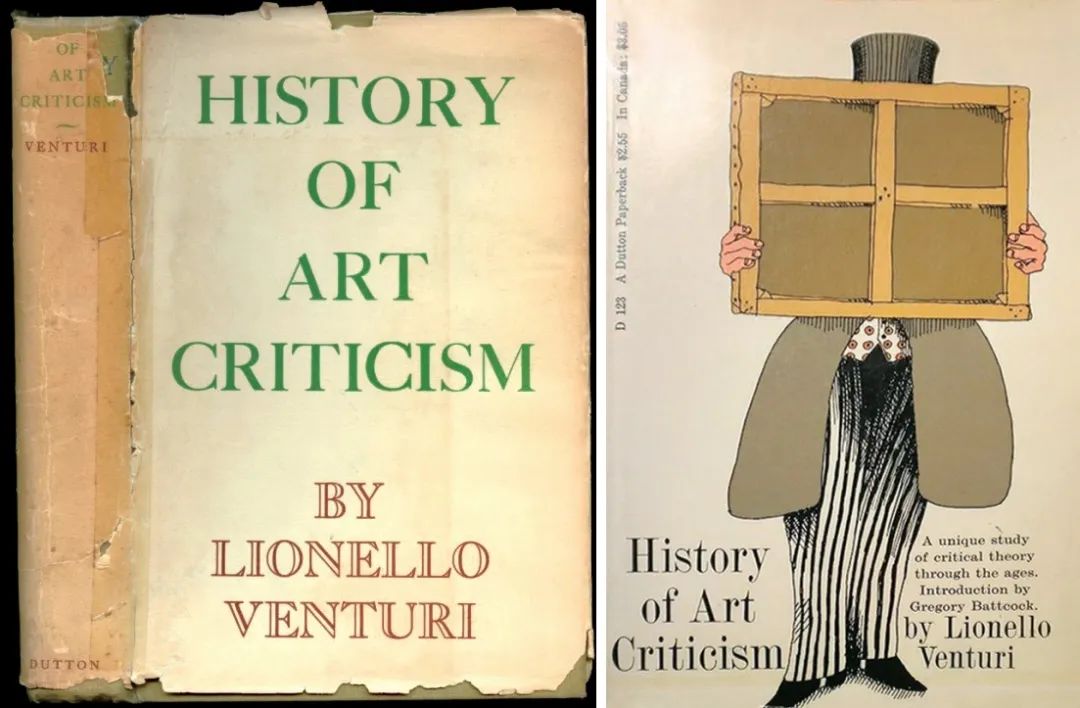
图 1 ˉ 左:Lionello Venturi,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trans. Charle Marriott(1936)。右:1964 年英文版,中文版即据此版翻译;此版比 1964 年意大利文版多出“批判性的艺术史研究”一章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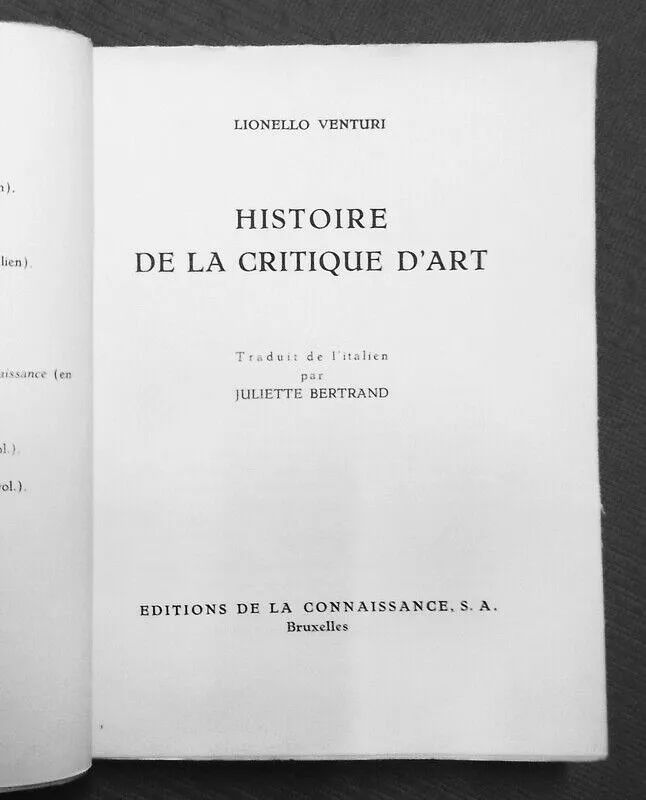
图 2 ˉ Lionello Venturi, Histoire de la critique d'art.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Juliette Bertrand(Bruxelles:Éditions de la Renaissance 1938)(据作者意大利文手稿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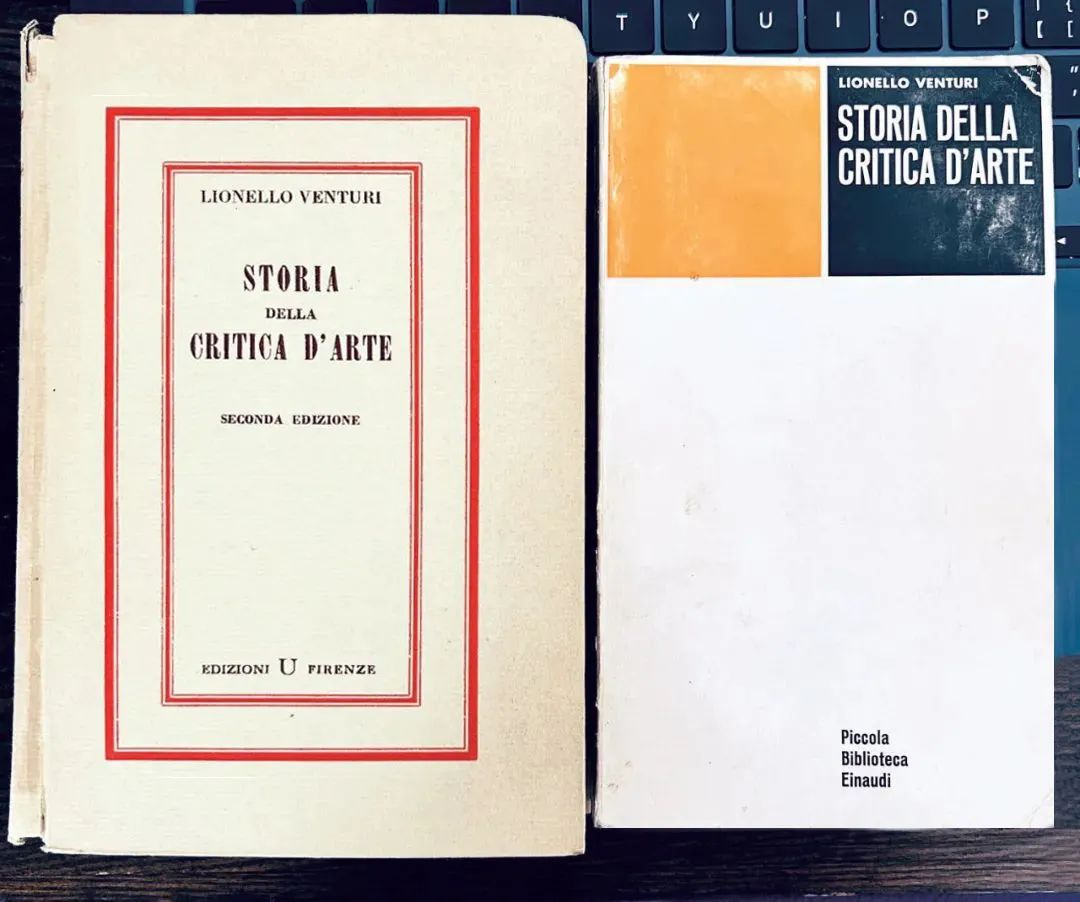
图 3 ˉ 意大利友人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教授赠予《艺术批评史》商务印书馆中文版译者的意大利文 1948 年与 1964 年两版(两版内容一致)
1936年英文版《艺术批评史》的发行,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文杜里除了于此书出版前已出版《早期艺术家的趣味》[Gusto dei Primitivi](博洛尼亚[Bologna],1926)与《批评家的托词》[Pretesti di critica](米兰[Milan],1929)两部专著,还在《艺术批评史》中收录了更早几篇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艺术批评与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La critica d’arte e Francesco Petrarca],1922;《沃尔夫林的方案》[Gli schemi del Wölfflin],1922;《纯粹可视性与现代美学》[La pura visibilità e l’estetica moderna],1923;《彼得罗·阿雷蒂诺与乔治·瓦萨里》[Pietro Aretino e Giorgio Vasari],1924)。其他更早之前发表的文章,不仅表明作者的文化关注,而且还说明他正越来越明确地寻求新方法与新视角以解释艺术现象。作者早在1917年便已着手这些具体的研究,其标志就是发表在《艺术》[Arte](第20期,第305—326页)上的《意大利14与15世纪的艺术批评》[Critica d’arte in Italia durante i secoli xiv e xv]一文。作者之后于1922、1923和1924年又分别在《美术公报》[Gazette des Beaux-Arts]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标题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批评》[Critique d’art en Italie à 1’époque de la Renaissance];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我们记得的有讨论拉斯金[Ruskin]的文章(载《词语》[Parola],1926),以及讨论14世纪末艺术批评的文章(《艺术》[L’arte],1925年第33期)。紧随上述文章的发表与《艺术批评史》的初版,文杜里继续从事着其他研究直到其活跃时期的最后几年:《艺术批评的理论与历史》[Théorie et histoire de la critique](载《艺术与美学》[Art et esthétique],1936),专著《当代艺术批评》[Art Criticism Now](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1),《19世纪初的艺术学说》[Doctrines d’art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载《文艺复兴》[Renaissance],1943,第50卷),《艺术与趣味》[Art and Taste](载《艺术公报》[Art Bulletin],1944年12月),《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批评》[La critica neoclassica in Francia](载《造型艺术》[Arti figurative],1945,第1—2期),前文提过的《现代艺术的理论前提》,以及《乔治·瓦萨里的艺术批评》[La critica di Giorgio Vasari](载《瓦萨里〈名人传〉初版四百年国际研讨会公报》[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per il IV centenario della Ia edizione delle “Vite” del Vasari],1952)。最后,我会记住廖内洛·文杜里所作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专论批评家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成就(《阿波利奈尔,一位镜中的伟大批评家》[Apollinaire,un grande critico allo specchio],载《快讯》[L’Espresso],1961年8月27日)。
上述整个系列的写作都向我们证明,文杜里感觉到对一种方法的关注与需要,这种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艺术史视为艺术批评史,而这种方法在我们看来代表着他对艺术史学[storiografia artistica]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么也应该这么说,自他从事艺术研究开始,或至少从他达到完全自主的思想之时开始,他都试图克服单纯的文献学[filologia]。克服单纯的文献学对他来说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对不同历史时期构成艺术家趣味[gusto]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作出了解释。此外,其价值判断[giudizio di valore]也是通过考察由艺术作品唤起数百年之久的批评反应而形成的。廖内洛·文杜里早在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913年出版的《乔尔乔内与乔尔乔内式》[Giorgione e il giorgionismo]一书里,便为其方法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显露出一种直觉[intuizione],就是需要一部艺术批评史,以助人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艺术家的经历。文杜里所解决的问题就是重现乔尔乔内的艺术活动,他从16世纪威尼斯[veneta]艺术收藏家米基耶尔[Marcantonio Michiel,1484—1552]留下的少许提示开始;但如果米基耶尔的少许提示构成了文杜里的研究基础,那么在另一方面它并不足以让这位艺术史家首先考察乔尔乔内之出现赋予威尼斯画坛的意义,这便完全基于他自己的后续研究与发展。这如此重要的意义不仅与画家、绘画技巧或方法有关,还涉及所有这些方面的汇合及其他方面,最终就是作为一种文化中至关重要、有意识且因此而成为关键时刻的乔尔乔内式[giorgionismo]。
在其1919年出版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批评与艺术》[Critica e l’arte di Leonardo da Vinci]一书里,重构艺术家活动的问题再次出现并得到更明确的详述,且涉及艺术家本人的观念。应当记住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杜里是最早关心构成艺术家文艺思想[poetiche]观念的批评家之一,并先行采用了我们今天称作文艺思想批评[critica delle poetiche]的方法。他就莱奥纳尔多提出的问题是:他身上的艺术家观念与科学家观念能分离开吗?能简化为不同类型的活动而且相互封闭吗?显然不能。因此,该著有机连贯地叙述了从莱奥纳尔多的艺术理论假设,经过其合乎常情的视觉形象与艺术上的偏爱[preferenze],达至其智力需要的全过程。在对这位大师作品作出评价之前,文杜里重构起因这些作品而产生的批评传统,这一程序对于达至价值判断必不可少。所以也就在此时,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趣味的概念,它关涉孕育出作品的文化领域、作品的环境、个人偏爱;需要清晰地确定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史,目的是能够阐明价值判断。
文杜里1926年出版的《早期艺术家的趣味》巩固了其方法论的构成,并代表着其批评思想的初次有机体系化。他说:“本书的撰写意在把艺术中体验[esperienza]‘默启’[rivelazione]所起的作用引入现时的艺术批评,而且不限于单一的人格并要从尽可能多的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本书不讨论这位或那位或多位早期艺术家的艺术,也不探求确定艺术家的是什么,而是探求使他们联结起来的是什么,不是他们的艺术,而是他们的趣味。我不知道‘趣味’一词是否最适合用来表达我的意思,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适合的词。为了避免误解,我声明我所说的趣味意指艺术世界里某一位艺术家或一群艺术家所具有的一系列偏爱。”接着他就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而举例说明某些偏爱,强调米开朗琪罗如何喜爱立体造型[forma plastica],这种偏爱“对米开朗琪罗及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佛罗伦萨画家来说”又是如何普遍。他由此作出推论:“从这个意义来说,‘趣味’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流派或潮流中的艺术家联结起来,无论你想把它叫作什么,它是一条为了理解个体艺术而必须遵循的道路。”本书旨在讨论“那些具有默启趣味”[avevano avuto il gusto della rivelazione]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又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从奇马布埃[Cimabue,约1240—1302?]到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约1445—1510]等早期意大利画家,第二组包括19世纪的几位大师。对艺术批评史的需要在讨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明。文杜里声称:“艺术从属于默启,艺术批评则不是这样。如果艺术批评想要理解默启的现象,就不能使自己屈从于默启,而是要运用自己所有的方式,那就是理性[ragione]的方式。事实上,只有理性才能在非理性的现象中发现理性主义的[razionalistica]入侵这一错误,发现自己除了记录这一错误的历史外别无他法,去逻辑认证[dialettizzare]这一错误的后果,追溯独立自主的主张,及追溯致力解放与互相调和的尝试。”
毫无疑问,《早期艺术家的趣味》提出了一些严肃的理论问题。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否认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美学原则的问题,而是根据克罗齐不具有的艺术体验与批评家而非哲学家独有的悟性[sensibilità],去解释那些原则的问题。除了要解释趣味这一概念,要建立去除了有关艺术发展或衰落等偏见的艺术批评,《早期艺术家的趣味》一书,正是通过将真正的“早期艺术家”作品与例如那些印象派[impressionisti]画家的作品做比较,再次断言需要一种阐释,即通过文艺思想的分析而不限于不可改变的类型,并且要考虑艺术家的个性,他们在历史上就是自己时代的参与者。这才是一部真实的艺术批评史的必要前提。艺术史家和批评家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1909—1992]曾就《早期艺术家的趣味》一书评价道:“使批评成为批评思想的合适对象,意味着承认作为一种价值的艺术作品并不存在,除了辨认出作品本身的这种判断;但恰恰是判断的程序、体验作品及开始把作品确定为一种价值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显得格外不同而且难以概括为统一体。对这个根据逻辑认证的统一体作出解释,而不消除这一结构中的历史复杂性,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文杜里批评思想的主要目标。”(《贝尔法戈尔》杂志[Belfagor],1958年第5期)
正如我们所能见到的,恰恰是因为此时宣称要写一部艺术批评史的愿望,以及批评家应对作品作出判断的要求,假如他不否认,那么文杜里无疑是自身突破了克罗齐思想的局限并转而面对上述关注点,而同辈学者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到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都会将面对上述关注点描述成他学术生涯最后那些年的特征。与此同时,他致力于建立新的艺术批评,他在写作与研讨会中,以及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都持续地努力着。1933年,他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办的艺术史大会[Congresso di storia dell’arte]“艺术批评的现时问题与指导观念”[problemi attuali e idee direttrici della critica d’arte]专题小组里,发表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言论。有关这次大会的报道及有关他在会上所述观点的说明,都包括在发表于1936年《艺术与美学》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里(该文的意大利文本以《艺术批评的理论与历史》之名辑入1956年出版的《评论文集》)。他在文中说道:“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艺术史家,我们努力使自己有关艺术家所作所为的认识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文献学可以详细叙述我们这个反而包含价值判断的学科;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在艺术作品方面的体验,是否赋予我们权利以确立审美法则这一由哲学体系胜任的工作。”他接着又说:“文献既已存在且大都得以出版,人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阅读它们、解释它们和使用它们。艺术家本人对自己艺术的思考,如果能够为我们所知,那当然是最珍贵的文献。但十分常见的却是,同一位艺术家的思想与艺术之间并不一致,甚至还相互抵牾。此时则有利于讨论如何辨别艺术家所属的文化及其想象力,阐明想象力在何处超越思想之外。同样,艺术家的同时代人,不管是不是他本人,他的学生还是他的追随者,他们的思想给艺术批评也都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因为在作者离世后,艺术作品的生命延续在自己所创造的传统中,这个传统又由于新作品的贡献而得到充实;后世的评价也应得到了解、比较和讨论。”于是,艺术批评史便以一种解释性的方法论与对艺术作品价值的探求而呈现出来。艺术史这一被文杜里认作等同于艺术批评史的学科,就不再仅仅被人们理解为风格的比较与可能的重构文献学文本。
就这一点而言,廖内洛·文杜里于1936年出版的英文版的《艺术批评史》,便全然不同于尤利乌斯·冯·施洛瑟[Julius von Schlosser,1866—1938]的那部基础性著作《艺术文献》[Kunstliteratur](维也纳[Wien],1924年)(图4)。他在此书“导论”的最后一段说明了“本书的目的就是艺术判断”。所以《艺术批评史》不仅对从古到今涉及艺术创作的审美与批评观念作出概述,而且对这些观念作出批判性的考察;这种概述与考察得以进行,有赖于作者必要的思想参与和对艺术创作的历史体验。尽管文杜里并不打算写一部新的美学史,然而《艺术批评史》还是被解释为“一部影响艺术判断的审美观念史”(阿孙托[Rosario Assunto,1915—1994],《“趣味”概念与艺术哲学家》[Il concetto di 《gusto》e la filosofa dell’arte],载《今日艺术》[Arte Oggi],1962年第13期)。批评家文杜里从[克罗齐]纯粹直觉的九霄下降,开始查看所有历史与文化环境如何得以解释,并最终落实到艺术作品。艺术家自己的偏爱说明是“艺术批评的开始”;可是他明确说明“没有共同观念的批评,没有个体要求的判断,是一种批评倾向、一种批评欲望、一种感官判断。它还不是艺术或者批评,它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是个体的并可以属于一群个体。它不是批评,它是趣味”。

图 4 ˉ Julius von Schlosser, Die Kunstliteratur : ein Handbuch zur Quellenkunde der neueren Kunstgeschichte(Wien, 1924)
至于对历史与批评的确定,文杜里直接引证了克罗齐的假设,即历史的解释与审美的批评极为类似,文杜里还声言艺术批评史“就是对每位艺术家身上艺术与趣味的关系作出说明,对艺术作用于趣味作出说明,对趣味反作用于艺术作出说明”。可以清晰地看出,廖内洛·文杜里具有上述构想及所声称的必要的艺术体验,从而超越了克罗齐的假设,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凭借对艺术制作的批判性体验而实际拓展了那些假设。最终,如果对克罗齐来说,历史是对行动的意识,那么对文杜里来说,艺术的历史可以也应该存在于意义之中,这种意义源于所有非艺术的——用克罗齐的话说——非想象性直觉[intuizione fantastica]的事物发展过程,但它们也都是艺术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对体验的价值认识,对艺术创作的敏感;之后,文杜里就会被上述的假设引导,去指责克罗齐;因为前者认识到,在后者的美学理论阐述里,在被其视为创作顶峰的时刻,以及对行动与直觉之间所作的阐述中存在着某种漏洞,还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没有考虑到技术、材料、想象力的各种因素,这些都是趣味的组成部分,而艺术家的个性有意地开始行动正是在趣味方面。
人们现在容易理解,为何采用类似的理论态度和不放弃考虑每件艺术品的批评方法,而使所有现存且便捷的方案与分类烟消云散;为何绝大多数人曾经理解成和依旧理解成经典的东西不见踪迹,或者证明是虚妄与谬误,也就是某种可模仿却达不到同样完美程度的东西。比如文杜里甚至可能从18世纪的作家和理论家那里借用了趣味这一概念或词语,摒弃了新古典主义者[neoclassici]对古典艺术的解释,这种解释被认为是错误的,还应归咎于它对于历史的抽象图式化表述。可正好相反,文杜里甚至废除了那种方法并且断言,假如凭借自己所处时代的艺术体验来看待往昔的艺术,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会更为深刻。艺术史具有“艺术批评的功能”[funzione della critica d’arte]这一说法由此得以证明。批评家不能只是待在等候区域去作出事后的判断,而要以自身的辨别与解释能力积极介入到艺术情形的中心。批评家“热情”[passionali]而非消极的反应便成了时代趣味的一部分,这种热情反应不是强加各种戒律而是通过协作与相互逻辑认证,从而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做出贡献。正是这一极为谦逊地主张批评家必须和持续在场[presenza]的要求,使廖内洛·文杜里的批评思想在今天依然无可争辩地切题与正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