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柴尔德——《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中译本读后
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解读柴尔德”系列丛书共四本,其中《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英文原版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V. Gordon Child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0)对柴尔德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经历着墨最少,几近于无,而是完全围绕他的学术研究,李零称其为学术性传记(“代总序”第9页)。但对柴尔德而言,他的史前史研究与当时的政治走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在某些时候甚至直接改变了他研究的基调。作者芭芭拉·麦克奈恩(Barbara McNairn)在书中重点讨论了柴尔德对欧洲和近东史前史所做的综合性工作、他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对“三期说”的阐释,以及他研究中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背景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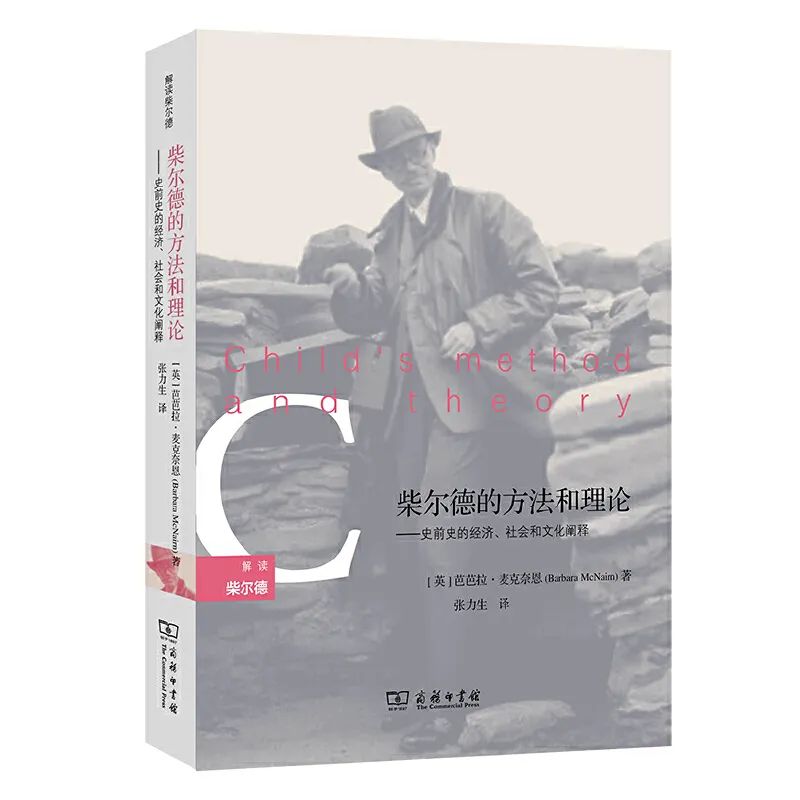
《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
作者:[英]芭芭拉·麦克奈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译者:张力生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柴尔德的学术研究之路显示出明确的阶段性。最初他对雅利安有着浓厚兴趣,致力于发现印欧人的起源和确定其原始文化(本书第1页)。探寻史前史,是为了发现现代欧洲社会先进性的史前基础(本书第9页)。“早期五书”——《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雅利安人:印欧起源研究》(1926)、《远古东方:欧洲史前史的东方序曲》(1928)、《史前多瑙河》(1929)、《青铜时代》(1930)基本都是为此而作的。柴尔德从来都不否认“传播”对社会文化变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还称不上是传播论者,因为他并不否认接受者本身的创造性,这是他试图调和东方传播论和欧洲文化的独立演化说的努力(本书第10页)。在青铜时代之前,欧洲受惠于东方文明的传播,东方领先西方;在青铜时代之后,欧洲沿着自己的道路独立发展,西方逐渐超过东方,并发展出彼时地球上最先进、最有活力的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柴尔德最开始主要是从语文学的角度探索印欧人的起源,他认为印欧语对促进智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强调雅利安人作为西方文明创始人的突出贡献(本书第21~24页)。此时柴尔德离种族主义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如果要追问雅利安人“非凡的精神天赋”从何而来,终极解释恐怕只有神学和生物学了。柴尔德本人就指出原始雅利安人凭借生物学上的优势征服其他民族,并传播自己的语言。而当这种对欧洲文化先进性的种族主义解释在日后愈演愈烈时,柴尔德及时掐灭了自己思想中危险的火苗,因为他很清楚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f Kossinna)所主张的“印欧人神话”在科学上和道义上都是立不住的,出于不被纳粹主义利用的考虑,他不再谈论欧洲史前文化的进步性。这一转变在《青铜时代》中就有所表现,虽然柴尔德不否认欧洲的青铜时代和现代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但是对前者的先进性持怀疑态度(本书第29~30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才重新关注青铜时代欧洲的创新性,但是彼时的叙事方式已经有了大变化,他已经放弃使用“雅利安人”的概念(本书第25页)。此一举动的连锁反应是在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柴尔德所持有的态度愈加谨慎。《史前欧洲的种族、民族和文化》(1933)对题中的三个概念进行了界定,避免将文化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race)相对应(本书第56页)。
在前期,柴尔德的研究路径主要是文化-历史的,关心特定族群及其物质遗存在时空中的分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此一阶段,柴尔德研究中的历史和哲学理论背景还不突出,或者说柴尔德还未形成理论自觉。物质遗存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说不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本身,就足以编织出欧洲的史前史。但他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史前史。在后期,柴尔德的关注点转向社会考古,也更清楚地表达了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从来不认为任何模型可以预测历史,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书第147页),他也不像某段时期内的苏联学者不加批判地对考古材料进行“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对柴尔德研究史前史最大的启发可能是为后者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的视角。他曾从功能经济学的角度对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的“三期说”进行了重新阐释,赋予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以经济发展阶段的内涵,将历史发展时间顺序的模型抽象为社会类型-阶段。这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做法的继承,而视特定技术与某一社会和经济形式相对应的主张(第95页),则表明柴尔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
与之前的人相比,柴尔德显得太过“科学”;与之后的人相比,柴尔德又不够“科学”。在牛津,柴尔德接受的是古典学训练,后者的传统是关注成熟的地中海文明中那些高级物质文化以及承载了伟大思想的文本。与之相比,他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发掘的斯卡拉布雷遗址(Skara Brae)就显得相形见绌,这是一个史前小村落,只有几座石屋和石制家具、石和骨制的工具、陶器,唯一珍贵的可能是一些串珠项链。但柴尔德没有低估它的价值,斯卡拉布雷恰恰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例证,成为他写作《苏格兰人之前的苏格兰》(1946)的绝佳案例。将视线聚焦于“伟大”之外的寻常遗存,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是科学地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所必备的素养。此外,柴尔德否认在历史进程之外存在任何现实的来源,也不存在超越现实的永恒法则,历史进程具有自足性(本书第127~128页)。能被历史学家的理性所认识的是趋势,而不是规律(本书第129页)。这是柴尔德对历史的性质和历史学边界的认识。
柴尔德的不科学体现在他提出了很多未经检验的假设,其中多是和传播问题相关的,在绝对测年技术出现之前都无法对其进行验证。欧洲史前文化的年代比柴尔德认为的还要早上几个世纪,很多据信属于近东的发明实际上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更早。比如伊比利亚巨石建筑的起源问题,柴尔德倾向于东方起源说,但后来证明他错了。又比如他对特洛伊青铜文化和多瑙河流域文查文化(Vinča)关系的判断也被证明是错的。他费尽心力构建的史前欧洲框架被新的测年方法颠覆了,连同他设想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及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和整体特征的看法,都失去了立论的根基。然而,我想柴尔德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放射性碳素革命”(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他很可能会奉其为第四大革命(其他三大革命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他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改即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惧承认错误的真正学者。然而,他是死得太突然了。
柴尔德时常说些戏谑的俏皮话,或以出格的着装和行为解构刻板的传统与教条,但他绝称不上玩世不恭。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柴尔德也对人类的命运抱持乐观的态度,深深相信“进步”始终是历史发展主旋律,这在他的《人类创造自身》(1936)、《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进步与考古》(1944)等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命运,柴尔德几乎从来都是悲观的。他曾不止一次表达过自杀的明智性,但没人清楚是什么促使柴尔德付诸行动。可能是对衰老的恐惧,也可能是对自己不再能产出什么创造性贡献的担心,又或者是对处于“冷战”中世界前景的深深绝望。哪个才是最后一根稻草已经无从知晓。总之,他还没见到最后一本书《欧洲社会史前史》的样书,就魂断蓝山(Blue Mountains)了。
柴尔德在爱丁堡大学执教了19年,但从未试图建立一个学派。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他销毁了日记和书信。柴尔德生于澳大利亚,远离大陆,也许他命中注定就是一个独行者,一个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