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谈 | 谢其章:E时代的深度阅读与纸质书收藏
在E时代,书的载体和介质非常多元,我们该怎样看待纸质书的存在?
有人说,纸质书会越来越走向精品化、收藏化,那么纸质书的收藏门槛到底有多高?怎样从书中发掘真正的乐趣?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记者专访藏书家谢其章,与他谈起了这一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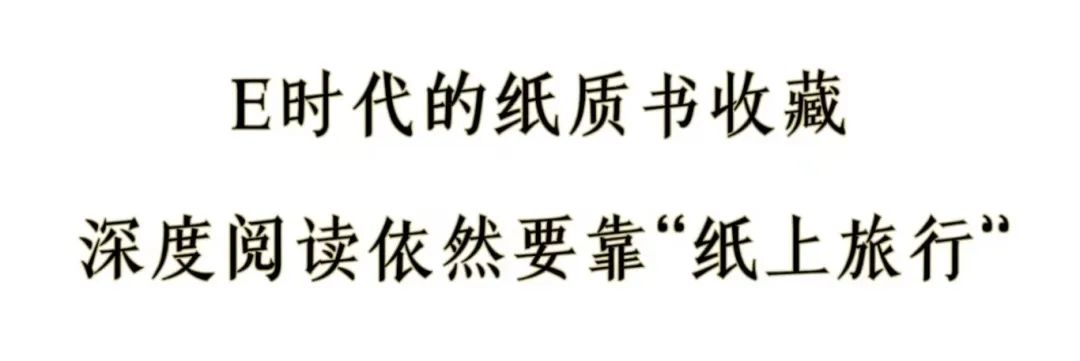

他既有自称为“老谢”的亲切随和,也有不被“藏”字所束的桀骜之气。回顾40余年与书为友的经历,谢其章总结出一番独属于自己的乐趣:边淘,边藏,边读,边写,将书中的知识化为己有,为己所用。经过日积月累,纸质书几乎占据了谢其章家的所有空间。面对当下阅读载体的变化,谢其章认为,纸质书爱好者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品质:定力。
电子书、听书、播客……打开手机的应用市场,有关资讯阅读的各类APP争先恐后地映入眼帘。“无纸化”推动了视听融合,人们在“阅读”这件事上的选择变得多元化了,似乎几英寸的屏幕就能涵盖浩如烟海的纸质世界,使得“捧上一本书”“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不再那么令人向往。“30年前,就曾有媒体探讨过这个话题:‘纸质书会被电子书取代吗’,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二者谁也无法互相取代。”谢其章形象地将读书这件事比作一块蛋糕,电子阅读的出现只是分走了其中一块,改变了纸质书一统天下的情况。
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并存的前提是尊重选择,尊重差异。电子书便捷、碎片式的阅读更符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与实体书的仿真度上大有研究创新,很是“吸睛”。谢其章也会用社交软件看书摘,“但看久了疲劳,对眼睛有害,不可取。”真正的阅读必须是深度阅读,这一点只有纸质书才能做到。
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纸质书的功能较之前更多偏向于收藏,谢其章认为:“这种定位太简单了。我收藏书,也会去读书,藏书和读书这两个概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况且不是所有的书都有收藏价值。”谢其章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成果,边读、边藏、边写是他的特色。他将自己的藏书心得记录下来,打磨凝集成一部部作品,命名为“文化随笔”,旨在打破“藏书”令人望之俨然的刻板印象。“我常常读闲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但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把一本书消化透。心得如果不及时记录,时间长了自己也会淡忘,况且成书后还能与读者交流,这也是我的一大乐趣。因此所谓的‘职业藏书人’、‘职业读书人’的提法都是被束缚住的单一思维。”另外,他强调读书切忌偷懒、猎奇,“只有这样,才能在旧书中感悟新知。”
谢其章20年前出版的《旧书收藏》,如今看来,依然是一本十分全面的藏书类入门普及读物,内容包括旧书收藏的基础知识、旧书收藏的分类(如毛边书、线装书等)、藏书票、藏书的目录指导、买书的经验、旧书的保值等。一本书要想成为藏品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谢其章认为收藏有几大原则:“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物以稀为贵’,印量要少。新出的书,印刷量很大的书不能纳入藏书范围。藏书的价格和价值是两回事,价格要交给市场来评定,价值就只能交给时间,这里就涉及一个‘沉淀’的问题。古书和旧书都需要沉淀,经过时间和历史的磋磨,书籍有了自然磨损的痕迹,这样才有收藏价值。今天的新书为了吸引读者,会在装帧中用一些新方式,读者想要收藏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意义不一定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能够随着岁月的洗礼而“增值”,“这是读书藏书除了融会新知、怡心养性之外的目的。”
谢其章专题收藏民国老期刊,同时他对“十七年文学(1949年—1966年)”著作格外关注。“十七年文学”书写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传奇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在纸质载体上的延续,是诞生于我国历史文化土壤的一块瑰宝,但其作为藏书的专题概念却具有滞后性。“‘十七年文学’里最有成就、有收藏价值的是长篇小说,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等,在出书当时的印量可达几百万,但收藏价值却时至今日才体现。这又涉及藏书很关键的一点:‘品相’问题。当初大家阅读的时候没有保护意识,导致现在要找到一个品相在九品以上、带塑封的、不折角的、不脏、不沾水的很困难,尤其是小说和连环画,对这一点要求极为严苛。”
藏书专业性较强,要想成为藏书家具有一定门槛,这一点普通读者很难做到。谢其章认为藏书还讲究一个“专题化”,每个人的收藏各有特色。藏书爱好者在知识界各有所长,要想成功把这项爱好坚持下去,往往需要集储蓄、空闲、空间三点优势于一体,“因此想要对所有书籍大包大揽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将自己感兴趣的作家或书籍的种类都收集齐,那么就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可以称作‘藏书家’了。”

谢其章出身于中文专业,却选择会计作为职业,他自嘲“爱好不能当饭吃”,却将爱书这一嗜好做到了“名震藏书界”的地步。他本人深谙藏书之趣味,但这份趣味应是去“伪”存真后留下来的一方净土。谢其章为毛边书在当代中国的发扬作出了贡献,也是这些年来与姜德明先生成为忘年交的一大重要原因。谈到毛边书的前世今生、制作工艺、市场行情,他如数家珍,却也不避讳其“有障碍于阅读”这一缺陷:“有人称自己拥有一本毛边书,就好边裁边读,这是在给自己的阅读设置障碍,未必是一种读书趣味。其实外界对藏书界有一个误区,好像只要涉及‘藏书’二字,就认为是很高大上的一个概念,望而生畏。稍微懂些行情的会问‘你家有没有线装书?’,或者认为只有藏有古书那才叫藏书,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根据对藏书趋势的观察,谢其章认为,现在人们的收藏意识还是普遍淡薄了,去逛北京潘家园、琉璃厂,遇见的老面孔多,年轻人很少有“藏”的概念。
当下,短视频如空气一般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大众的生活,引导着大众的思辨方向,书界也在通过新技术不断满足着读者的新阅读需求。谢其章认为,当代人更应反思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定力”。缺乏定力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好多人都失去了深阅读习惯,捧着电子书碎片式阅读,很难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到头来一无所获。他说:“诸如抖音卖书此类,就像变相地在读书界‘追星’,从众的心理催促着人们去购买,但回过头来不一定读。一般情况下,一本书从制作到销售,需要考虑到包括编辑、出版界、读者在内的多方感受,然而现在线上售书的话语权往往和平台主播的影响力挂钩,这虽然能带来一时的效果,但对出版界和读书界是否有长远的积极的意义,值得思考。”
谢其章作为藏书家,其定力体现在藏书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方方面面,藏书存放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由于住房条件有限很多书都装箱存放。他笑言:“习惯了纸质书,就算是看着它不去读心里也踏实。40年来积少成多,为了藏书把席梦思全扔了,床底下有三四十号箱子摞着,只是找起来不大方便。”大规模地藏书,家中却整洁有序,谢其章自我调侃是“强迫症”,不喜欢把书横七竖八地杂乱放着,哪怕平着放,只要罗列好,那也是一种美观、一种境界所在。细节方面,如在书籍上记眉批的习惯,也让谢其章深感其乐无穷。

谈及藏书的归宿,他认为生前以书为乐,“大爱必费”;身后或许会“多藏厚亡”,无论是像唐弢、郑振铎一般的前辈交由公藏,还是像姜德明一样的大家,其旧藏走上拍卖,都难以预料。但淘书、藏书的传统一代接一代地流传至今天,只要保持本心享受过程,做好当下事,就可尽己所能感受到书的乐趣,为藏书界、读书界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