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考古学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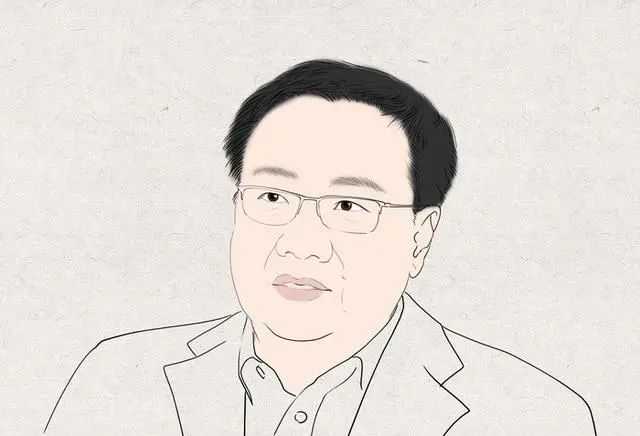
采访时间:2022年12月
那个时代,大家都学得如饥似渴,非常充实
我是1980年考入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经历过“文革”,大家都非常珍惜失而复得读书的机会。入校一个学期的时候选择专业,我选了考古专业,希望能在文献研究历史之外多一种技能,能以实物的形式研究历史。当时知道考古的人并不多,上大学之前对于专业也没有什么认识,入校之后知道有这么个专业。
 1980年10月1日,入校不久的方辉与几位同学在济南百货大楼对面的人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第一张西装照。
1980年10月1日,入校不久的方辉与几位同学在济南百货大楼对面的人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第一张西装照。
山大的考古专业是1972年建立的,到我入学的时候还不到10年的时间,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专业,但是凭直觉感觉到考古还是很实,很吸引人,尤其是觉得学这个专业不光能够在书斋里边,而且还能够到野外考察,能看遍名胜古迹。当时对这个专业也就是这样一知半解,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只是凭一种感性的认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当时我记得我们年级是120多个人,选考古的有80多个,还是经过了筛选,各种身体指标达标之后才进的专业。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考古专业的特色还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以实物研究历史。老师们课堂上讲的、我们在教材里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器物、实物,包括器物的照片、线图,这个是和学科发展的时代性和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因为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器物的年代。学术界目前是以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命名,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标志。如此算来中国考古学也就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建构考古学的编年史,或者叫考古学文化史,器物和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问题是核心。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我国的考古学走过了60多年的时间,但年代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实际上即使到现在为止,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或时空框架仍然在建构的过程中,而建构这个区系和框架需要研究大量的出土器物,用器物类型学来判断它的年代。所以当时的课堂所学,包括我们平时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的陶器、青铜器,都是年代学的一个基本功。也就是从这种对文物的感受当中,你会发现文物不光是简单的一个器具,它还能标志年代,所以要求学生记很多东西。当时没有复印机,同学们怎么来记忆这些东西呢?就是用硫酸纸,有的时候没有硫酸纸,就是白纸,用铅笔一遍一遍地描,以强化记忆。旧石器考古记石器,新石器记陶器,青铜时代记青铜器,到了历史时期要记大量的瓷器。这是基本功。这样在野外发现了同样或类似的东西,哪怕是一块残片,你都会对它们的年代有一个判断。当然除了器物之外,我们也看古代的房屋、窑址等,考察城市、墓葬的发展演化等,还包括手工业作坊,以及与艺术有关的各种雕塑、壁画、彩陶等等。对古代艺术品的关注与山大考古的特点有关。因为我们的专业和学科奠基人刘敦愿先生,他是美术史出身,做美术考古和美术史非常有名,尤其是在青铜器纹样及其含义的解读方面,引领学术前沿。另外李发林老师做汉代画像石研究,也很有名。所以我们也受到了美术考古的熏陶。
 1982年,拥有一台录音机算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为了支持方辉学好外语,父母还是下狠心给他买了一台。
1982年,拥有一台录音机算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为了支持方辉学好外语,父母还是下狠心给他买了一台。
也因为如此,自己对青铜器比较感兴趣,对于青铜器的图样及其内涵比较感兴趣,在自己的阅读当中,与之相关的知识领域也都有所涉及,比如艺术的起源,还有古文字。古文字和古文献,是研究历史、考古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学好考古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好的历史学的训练。我们学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包括一些专题课。大学这四年我感觉还是很充实的,就感觉时间不够用。记得当时可读的书不多,我们能看到的杂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我们班里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都订阅了《文物》《考古》。我从1981年开始订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当时感觉到考古研究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来作为基础,来建构我们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所以大家学习的氛围很浓,不论在课上还是课下,大家都学得如饥似渴,非常充实。
到了毕业的时候,选报研究生,就要作出一个抉择:读哪一段?说实话,当时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取向,但是自己感觉还是对青铜器比较感兴趣。那时能够带研究生的导师很少。一个是刘敦愿先生,他搞青铜器研究,搞美术考古,还有一位是蔡凤书老师,他做史前考古。我就选择了跟着刘先生来读硕士研究生。说实话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就是按照自己学习的基础,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我们班当年就考上我一个,那时招生指标少,报考的也不多,一般一个专业一年也就招那么一两位,大家觉得学了4年了,就业参加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向。
田野实践、“年代学”训练和“聚落考古”的国际视野
1984年毕业,正好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那时候中国的考古学界和国外的考古学界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交流了。1984年,我记得应该是春夏之交,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应邀来国内讲学,他选择了北大和山大来作他的巡讲,讲的题目都是考古学前沿的问题。他准备了6个专题,后来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为题出了一本书。
那时候我本科刚毕业,即将进入研究生阶段,张光直先生的讲座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我们发现,海外也有关注中国考古的这样一批学者。不光中国学者,实际上全球范围之内,对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古代文明都有一批研究的学者,而且他们研究的路径、方法和我们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记得张光直先生在山大作了4次演讲,当时系里很穷,连幻灯机都没有。张光直先生一开始就希望有个幻灯机,因为考古是用实物来呈现研究资料,没有实物图像,很难说明白。但是学校连一台幻灯机都没有,可见当时的办学条件有多么的简单落后。
没有幻灯机,张光直先生就画,用粉笔来画,再就是事先提供一些材料发给大家。他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以年代学的建构为主了,不再是我们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搞陶器的分期断代,搞器物分型分式,他已经不讲这个了。对我冲击力最大的有两讲的内容,一是第一讲,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予以考察,提出中华文明是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体系,这种区别既表现在文明形态上,也体现在文明起源的道路方面;再就是有一讲叫“谈聚落形态研究”,现在也叫“聚落考古”,讲的是依靠我们已经建构起来的考古年代学基础,来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考古的问题。
当然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已蔚然成风,研究社会发展,探究社会怎么样由简单向高级演进,但是国内的文明起源研究,当时受到了像柴尔德文明三要素——城、冶炼、文字的影响,大家讨论文明起源,基本上是这么个模式。但张光直先生在这个讲座里面,讲的是怎样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聚落形态,注重区域内聚落分布的规律和模式,进而来研究区域社会的发展,也就是如何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开展考古学研究。这个和我们当时的分期断代、考古学文化属性的研究已经很不一样了。后来我们知道,欧美考古学当时已经完成了考古学文化史的构建,开始超越年代学重心,上升到了社会问题的研究,当然还有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环境问题,也自然受到重视。而要想做好这些研究,必须有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就是跨学科的研究。
坦率来说,张光直先生的讲座,我当时听起来是似懂非懂,尤其是聚落形态这个概念,我想不光我听不懂,我们的好多老师也不一定能够听得懂。这是一个重要转向,考古学研究重心的转向——尤以年代学的建构为中心,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研究的转化,包括和社会密切相关的环境。这个转向在开展考古工作较早的地区应该是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逐渐认识到,我们自己封闭了这么多年,我们和世界考古学之间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鸿沟。这个鸿沟主要是各自发展,我们基本上关注不到国外的发展,不了解国外考古发展到什么样一种水平。
考古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它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来说,1836年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说”的提出标志着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的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得到应用,包括航空考古、勘测技术、分析手段,尤其是1949年利比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大大促进了考古年代学的发展,在考古学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价值。在我国,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并命名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此后一个阶段战乱频仍,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考古学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环境,但随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加上“文革”的干扰,考古学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自我发展的阶段。尽管如此,在夏鼐、苏秉琦等前辈学者的指引下,考古工作者在各主要地区考古学文化年代学建构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当改革开放开门看世界的时候,发现西方已经在考古学领域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90年代,学术界进入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在考古学界内部,大家开始对考古学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对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阶段性、局限性也有了一些认识。从1984年到1987年,我在山大读研。其间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高校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逐渐增多起来,先是与日本、后来与美欧学界的交流日渐频繁,可以了解到海外学术信息。记得当时已经有一些留学生甚至国外的访问学者跟我们一块儿学习,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国外的专业图书,不断出现的欧美考古译作也被介绍进来,这就在学界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的转型问题的讨论,也就是研究重心从年代学建构向综合研究的转型。
总之,在山大七年一贯制的系统学习,为我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写论文,仍然还是按照我们所学的所训练的这些内容。我的硕士论文选择的是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还是传统的题目。因为我们课堂上学的,包括在野外发掘,大家关注到的还是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谁早谁晚的问题。发掘了材料之后,要对资料进行整理,首先要说清楚的就是它的年代。本科期间我们进行了两次发掘实习。研究生阶段对实习没有要求,但我也是参加了两次田野实习。这几次考古实习对我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第一次实习是在1981年的秋天,在新汶发掘一个春秋时期的墓地。因为发掘的是小型墓葬,比较简单,发掘出土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精美,主要是一些陶器和少量青铜兵器,基本上没有见到非常精美的青铜器,但第一次用双手发掘出来真实的文物,还是很兴奋的。当时是每两个同学一个小组,按照探好的墓口进行发掘。发掘结束后还沿汶河进行了考古调查。
实习期间,老师和同学们一块儿吃住、一块儿工作,虽然有些单调,但所受到的训练还是非常系统的。第二次发掘实习是1983年秋天,在山西侯马,是配合铁路的复线工程而进行,发掘的是东周时期晋国的一座古城。这两次考古发掘都是周代的,对我后来研究方向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侯马是晋国的中心,我们住在侯马工作站,出门就是和晋国有关的历史、文物。发掘时山西和其他高校的老师还经常到工地考察,作讲座,内容也都和晋文化有关。当时就觉得商周考古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后来选择青铜时代考古,跟这两次实习经历有关。
读研阶段,本来一次实习就可以,但导师刘敦愿先生十分重视田野实习,我个人也觉得应该多进行田野训练,所以也是实习了两次。常言道熟能生巧,考古发掘是一个体力活儿,但更是一个技术活,经验非常重要。你的发掘水平肯定和你在野外的时间是成正比的。刘敦愿先生就经常说,就像飞行员一样,飞行时间越长,你的技能就越高。研究生阶段的两次实习都是在泗水尹家城遗址。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做的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后来发表在一本论文集中。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
岳石文化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夏代,是夏代中后期到商代早期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是它的很多特点还和新石器时代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求学阶段这三年当中,无论是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理论方法的学习,还是田野考古训练,感觉还是收获了很多。这应该也是那个时期培养一位考古工作者通行的路子。所以到了1987年研究生毕业,我就顺理成章留在学校当了老师。

1983年刘敦愿先生在给学生上课
做商周考古不但要求具备扎实的考古基础,还要求掌握一定的历史文献。导师刘敦愿先生是一个文献功底非常好的老先生。从小读私塾,后来跟随著名古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丁山先生做助教。刘先生上课引经据典,古文献张口就来。他们那一辈在文献方面都下过童子功。我见过他年轻时用毛笔抄录的《春秋左传》,厚厚一大摞,肯定抄录了不止一遍。老一辈学者的文献修养,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献修养,当遇到考古学的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很快从文献知识的储备里边找到证据。现在的很多考古学者,在器物的训练上面可能有他的优势,但是比起老一辈学者,在文献的训练上依然是欠缺的。山大素以文史见长,这个史主要是古史。因此我们那时也常常会听到一些著名的文史大家来作学术报告和讲座。还有古文字学。本科阶段徐鸿修老师给我们上古文字课,也就30个课时,但是却引起我极大兴趣,此后也愿意花时间去阅读大量甲骨文、金文论著,慢慢领悟。后来我训练自己的学生,也要求他们必须掌握古文字、古文献的基本功。所以我感觉自己的知识面、知识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毕业留校后,我自然分在商周组,为刘先生做助教,刘先生当时讲的课,有时就让我去讲,记得讲过商周考古,也讲过古文字学,这也逼着自己多读一些古文字学的书,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后来我的研究方向,基本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以考古学文化和器物研究为主,包括岳石文化的分期断代、岳石文化的类型、岳石文化和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从山东这个区域角度来看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变迁及其与东方的关系等,写过几篇文章,应该来说反响还是不错。尤其是对于山东岳石文化和郑州商城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东方力量和夏商更迭的关系等,这些文章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其合理性。其中比如通过对(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来探讨商灭夏,认为商人是联合了东方夷人的力量才攻灭夏王朝的,东夷和商形成联盟之后,大约在二里头的三四期完成了灭夏。这是从东方区域考古学文化来看这个问题。这种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考古学证据的支持。此外,在夏商与岳石文化的交叉断代方面,我也提出一些看法,也就是岳石文化到了中原地区,它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哪一个时代?我指出了岳石文化最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一期没有,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上层晚段。岳石文化从二里头二期出现,一直到中商时代结束。随着后来考古资料的充实,上述观点到目前为止还都是能够站住脚的。这是围绕着岳石文化的研究。当然,有些问题现在仍然在讨论当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四十年过去了,但是岳石文化的资料积累还是比较有限的,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些动态,可以说,夷夏之间的关系,包括夷商之间的关系,未来肯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取向是我国考古学的一个特色,我们不能把历史排除在外,尤其是到了夏商周时代,考古学的历史取向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考古学界有一些学者反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认为这样一来考古学的科学性就会大受影响。我也反对在史前历史研究中与古史传说盲目地结合,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如此发达的国度,考古学从一产生就带着历史取向,就是用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回避这个问题也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说夏商的历史,恐怕考古学还是有非常大的发言权。但越到历史时期,文献越丰富,考古学的作用可能没那么凸显。实际上,在亚欧大陆,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是普遍存在的,不像北美地区缺少历史文献,考古学想使用历史文献都是奢望,他们后来与人类学结合,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也有学者认为用实物来建构历史是另外一条途径,它和文献历史是两条途径。在我看来,两条途径是殊途而同归,目标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
文献建构的历史有它的优点,它可以把一件事情描写得很具体,把一个事件说得很清楚,但是要知道能进入史籍里边的历史只是九牛一毛,大量的历史事件只能是湮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尤其是基层社会的历史。能够进入历史书写的往往是筛选的结果,是上层统治者书写的历史,一般关注不到底层社会。所以考古学在历史书写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关注王朝史,但更多的则是基层社会的历史。当然,考古学受其阶段性的制约,也有其局限性。考古学家关注什么,收集什么,描述什么,也自然受到流行的理论方法的影响,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理想的状态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应该更多地结合,取长补短。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大家常说教学相长,指的是教书与科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学校教课、带学生,不可能说我研究哪一段,就发掘哪一段,因为你还有学生培养的任务,需要“贯通”。而且,考古学者的成长往往和所发掘的遗址关系十分密切。幸运的是,无论是作为指导老师之一,还是作为一名领队负责遗址的发掘,我所经历的遗址发掘都比较丰富,每一次发掘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比如泗水尹家城遗址,邹平丁公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日照两城镇遗址,长清仙人台遗址,都是这样。在省外也做过像三峡工程这样一些抢救性的发掘。如果说对个人在科研方向比较重要的促进方面,仙人台遗址的发掘应该是其中之一。仙人台遗址在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北黄崖村南,位于南大沙河北岸的一个台地上。遗址的遴选是在1994年年底。当时济南市文物处刚刚完成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不久,发现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我校也希望在济南市开展考古工作。在长清博物馆的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北黄崖村民送交的两件保存完整的青铜簠。以此为线索,在文物处刘善沂处长陪同下,我和崔大庸老师等三人到北黄崖村进行考察,证实铜器出土地点就在一处名为仙人台的台地上。台地面积也就两亩多,便于全面发掘,一网打尽。1995年春天开始在这儿发掘。事先预计会出土青铜器,但没想到一下子发现了东周时期邿国的王室墓地,共六座,除了二十几年前被村民无意破坏的一号墓之外,还有五座保存完整的墓葬,包括据推测应该是邿国国君和他夫人的墓葬。这次发掘揭开了历史上有关邿国地望长达2000多年的谜团。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数量丰富、组合完整,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孔子时代追求的礼乐文明离我们如此之近。以此为基础学校成立了博物馆,青铜器成为博物馆最丰富的馆藏。青铜器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切切实实可以通过出土文物深刻感受到。

仙人台遗址远眺(由北向南)
仙人台青铜器的历史价值最直接的代表当然是铭文。因为邿国在文献里边,只在《春秋左传》里有简单的一句话,也就是它被灭国的时候,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夏,邿乱,分为三。”对它的地望所在,汉代及以后的人都不知道了。就这么个小国家,谁能设想有朝一日,它的墓地会在我们手下发掘出来。后来查找有关资料,知道清代晚期就有邿国青铜器的出土,但因为出土地点不详,对于邿国在什么地方一直以来是说不清的。按照魏晋时代杜预所作的注释,邿国应该是在鲁国以南,在济宁境内。此后这就是定论,影响2000多年。但没想到地处鲁北的仙人台一下子出土了邿国王室的东西。这就引起我们对杜预注释画了个问号:是杜预当年记错了还是什么原因?怎样来看待历史文献的这项记载?当然我们不能轻易否认杜预的记载。因为鲁国灭邿之后,把邿分了三个部分。鲁国南部的那个邿,可能是邿国的一支迁过去的,而长清、平阴境内的邿国,则是它的母国所在地。我们知道,鲁国是周礼的维护者,在灭一国之后,不会把它赶尽杀绝,因为这些古国都有渊源,国虽然灭了,但还要留下他的后人来延续香火,祭祀祖先。这就是孔子当时说的“兴灭国,继绝世”。鲁灭掉邿国应当也是如此。至于另外还有一支可能迁到了哪个地方,现在说不清楚。实际上,仙人台遗址也只是邿国的墓地所在,并不是邿国的都城,还不能说邿国的历史因为仙人台发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考古发掘有的时候可以补充和修改历史,但历史可能是很复杂的,要想接近历史的真相,也不是一次发掘就能解决的。邿国在两周之际,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晚期,我们这次发现了邿国国君墓地,说明这几百年时间,它的重心就是在长清附近。所以对于研究成文时期的历史,考古学能解决一些问题,在某些时候能解决相当大的问题。像这次考古发现,因为发现了7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把邿国的历史大大丰富起来了。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邿国还和姜姓的国家有通婚,这个姜姓国家很可能就是齐国。我们还知道,邿国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高度发达的青铜礼器、乐器,有按周礼来进行的丧葬习俗。考古学永远是这样,你能解决一些问题,再往前走,可能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你解释。

仙人台遗址出土的青铜方座鸟柱

仙人台遗址出土的铜簠
留校之后我参与发掘的遗址当然还不止这些,例如邹平丁公遗址,因龙山文化城址和陶书的发现荣获1991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很幸运,自己参与和主持的这些发掘,每次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一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发掘经历,还是很难得的。大家说我运气好。这里可能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往往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你在发掘前期的调研、准备的过程,到选择遗址,实际上已经在研究它了。后期的发掘成果最终还是建立在你对遗址的持续关注、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发掘的成果是对学术研究的最大回报。可以说这一系列的田野发掘的经历,都和我的科研息息相关。
大辛庄:商王朝经略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之间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我也有机会去国外进行访学。先后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通过到国外访学,自己的视野大为开阔。这4次国外访学,加起来恐怕有3年多的时间,对欧美同行们的观察了解更为全面,包括对流行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尤其是多学科交叉,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将这些理念带回来,并将其中有益的做法运用到我们的学科建设中。
2002年从哈佛大学访学回来,首先选择了济南历城大辛庄遗址进行发掘。从2003年到2014年我们对大辛庄进行了三次发掘,收获还是很大的。2003年我第一次独立带队实习。此前已经在日照两城镇开展了中外合作调查和发掘,发掘大辛庄遗址时我们已经开始注意把多学科交叉的思维运用在发掘当中。首先是对以大辛庄为中心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覆盖面积100多平方公里,搞清了区域聚落形态,确立了大辛庄遗址在商代绝对核心的地位。发掘中尽可能精细化地发掘,并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陶瓷器分析、冶金考古等,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幸运的是,那次发掘还首次在大辛庄遗址发现了甲骨文,揭露出大量的商代的墓葬,基本上搞清楚了大辛庄遗址从商代的早期开始,就已经是鲁北地区的区域中心。至于说它是个军事重镇还是一个古国,一开始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我认为它就是商代在东方的一个军事、行政的重镇,而不是一个地方国家,不是一个方国。大辛庄遗址所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和安阳殷墟有非常强的相似性,无论是体现礼制的器物,还是日常生活器具,都高度一致。
再就是从大辛庄出土青铜器的铭文来看,它的族徽是多元化的,不是一种,或者是少数的两三种。它是有多个不同族群的人同时埋葬在一个墓地里边,如果把济南市内刘家庄商代墓地也考虑进去,其族群的多元性就更加明确。它不像青州苏埠屯和滕州前掌大墓地那样的家族或宗族墓地,而更像是一种带有行政或者军事色彩的一些人物的墓地,这些人来源复杂,各有自己的族属,非常像一个行政中心。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似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又有自己的一个公墓。这是我判断大辛庄是一个政治军事中心的理由,它和我们知道的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墓地都是有一种最多是两种族徽组成的青铜器群,其他的铭文很少,这和大辛庄很不一样。

大辛庄遗址139号墓出土的铜盉

大辛庄遗址139号墓出土的铜鼎

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的甲骨卜辞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玉戈和玉钺
通过大辛庄遗址的发掘研究可以看到,济南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商王朝早期就已经被看好。它地处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往东顺着泰沂山北麓一直可以向东,贯通淄河、㳽河、潍河、胶河,直达胶东半岛地区。南北也是贯通的,现在的京沪线就是当年的交通线路。所以说济南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至少从商代,古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商代以大辛庄作为战略中心的原因所在。
明义士和他的藏品
提到商代考古,还应该提及我所做的一段学术史的研究,也就是关于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的研究。关注这个话题是个很偶然的机会。大约是1993年,我们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专业的宋家珩教授找到我,希望我做一下有关明义士的研究。当时她承担了一个项目,叫“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其中的一位传教士叫JamesMellonMenzies,中文名字叫明义士,因为他后来转向甲骨文和商代考古,出版过不少东西,需要从学术上对他进行挖掘。熟悉甲骨文和商代考古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当时对他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负面的,说他将大量中国文物盗运出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类。当时宋家珩老师找到我,她说你能不能做一做这个人的研究。作为一名考古学研究者,我对明义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甲骨文学者,也知道他在齐鲁大学教过书,那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接到这个课题之后,通过对明义士本人和传教士群体的粗浅研究,我发现传教士群体很重要。这些人在20世纪初或者再早一点的时候,把西方一些先进的医学、科技、文化传递到中国,确确实实带来了一些进步,而且他们及他们的后人在促进中加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明义士在安阳传教,1911年发现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安阳殷墟。当时国内学术界对甲骨文是商代遗物已经基本肯定下来,但对于甲骨文的出土地只是少数古董商知道。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虽然考证出洹上殷墟是甲骨文的出土地,但直到1915年才亲自到访殷墟。明义士发现殷墟之后,感觉自己一生跟这商代文化有缘,就开始用大量的精力来研究甲骨文,并于1917年出版了《殷墟卜辞》一书,这是西方人最早的关于甲骨文的著作。尤其是他在甲骨文上发现了“上帝”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启示。他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的信仰,发现中国的上古时期,“上帝”与西方的上帝一样具有非常大的神力,是人们信仰的对象,这和西方有相似之处,这个引导他一生开始进行甲骨的研究。他后来于1932年受聘来到济南齐鲁大学,教授考古学、甲骨文研究。到1957年去世的时候,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他是最早从事中国甲骨文研究的西方学者。
项目实施期间我两次去加拿大访学,都去了明义士儿子家。他的儿子ArthurMenzies,中文名字叫明明德,是加拿大第二任驻华大使,对促进中加友好作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们一家都和中国关系密切。通过对明义士的研究,我的语言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你必须读大量的英文文献。所以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一本小书,就是《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他的藏品里边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一些青铜器。我对这些藏品的来源进行了系统梳理。
这本小书,主要对明义士在甲骨文和商代考古方面的研究做了深入挖掘。这也逼迫我对甲骨文下了一番功夫。在明明德家里,我发现一册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时期的讲义《甲骨研究》,其中对于甲骨文的断代,早在20世纪30年代明义士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商王名字有争议的对应方面,与郭沫若同时期的论著观点一致,但因为这本讲义发行不广,看到的人很少,明义士的意见不为学界所知。此书由我写了序言,于199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再比如,明义士于1942年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商戈》(ShangKo),是对商代青铜兵器的专论,其中对于青铜戈的类型学研究和年代推断,不乏真知灼见。此书直到1965年才由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发行量很小,加之为英文版,国内几乎无人知晓。明义士的藏品分藏在国内的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国外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这是四个主要的藏品分布地点。这本小书中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追踪,把过去对明义士的一些不太确切的评价,也进行了一些纠正。随着对明义士本人的了解,我认为他确确实实当得起学者的称号。而且他从来不买卖文物从中牟利,这在很多西方藏家那里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他对中国充满了感情。所以我说明义士就是一个“文化上的白求恩”,实际上有关明义士的材料还可以进一步地挖掘,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对外关系也很有借鉴作用。这些传教士的后代对中国都充满感情,而且都希望中国和他们所在的国家能够和平、友好相处。好在后来又有董林夫先生的Cross Culture and Faith: 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MELLON MENZIES(《跨文化与信仰:明义士生平》,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于明义士生平研究得更为深入。
因为对明义士的研究,我还十分关注流散到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我们当然要搞清楚自己的家底儿。这些文物,怎么流传出去的,流传到哪个地方,不说能不能追索,但至少可以做到知情并介绍到国内,为大家研究所用。这是当前应该开展的一项工作。就像我们山大开展的汉籍合璧工程,就是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典籍收集起来,集中出版。文物流散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国没有文物保护法的情况之下,大量的文物流散出去了。现在应加以关注。
两城镇:国际合作和区域系统调查的意义
以上所谈基本上是我的科研和考古发掘经历。随着年龄的增加,近几年来直接到野外一线工作的机会少了,但自己的关注范围却扩大了。首先,个人不应该仅仅限于自己研究的小领域,还要对整个的学科发展有所考虑: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赶上,或者是至少能够追踪上世界前沿的水平?
首先需要对国际前沿有所了解。这得益于我们的中外合作。1995年我们开始了和耶鲁大学的合作。刚才讲到,张光直先生生前非常期待能开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考古合作,但是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他已经将近70岁了,他身体不好,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等他拿到批件的时候,已经不允许他再过多地做田野工作。他最初设想在山东做这样的区域系统调查、聚落形态研究。1984年他选择到山大做聚落考古的讲座,实际上是有考虑的,因为山东地区考古学起步比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城子崖,1930年就开始发掘。两城镇遗址也是早在1936年就开始发掘的。而且山东考古学家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就顺着龙山找到了大汶口,找到了北辛,现在找到了后李甚至可能比后李还要早的文化遗存。山东地区考古学的年代序列建构得比较完整,所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本上,已经建构起来了。这是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基础,没有年代学的这个基础,你想研究更深入的课题是很困难的。另外地处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比较丰富。可惜张光直先生后来没有完成遗愿,他的愿望由他徒孙辈的文德安教授实现了。文德安教授是理查德·皮尔森的学生,而皮尔森教授是张光直先生的弟子。
从1995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和耶鲁大学在日照以两城镇为中心的鲁东南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后来扩展到考古发掘。这个项目从199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2019年底因疫情受到影响。20多年的合作中,包括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成果斐然。先后参加这个项目的老师,既有像蔡凤书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当年正值中年的骨干老师如于海广老师、栾丰实老师,还有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因为持续时间长,考古系的几乎所有老师和研究生都参与其中。因此,聚落考古、科技考古在山东大学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实践过程。
首先是区域系统调查。1995年冬从两城镇遗址开始的考古调查,至今覆盖面积超过了4000平方公里,揭示了从距今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距今2000年左右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每一个时期聚落的分布形态,使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区域之内,人类社会怎么样从一个简单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一步步走向复杂化,发展到王朝国家,发展到帝国的历史。
这一张张的聚落形态图,看着很简单,无非就是这儿标了个小点,那里画了个大圈,但是这些点、圈,全都是考古队员用双腿丈量出来的。覆盖的区域和范围,从现在江苏、山东交界的赣榆区,一直往北走到了高密、诸城,跨越了日照、青岛和潍坊三个市。这种全覆盖式的调查看似笨拙、简单,但确实有效。所获得的资料是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非常基本的数据。调查方法一般是由5-7人组成一个组,每人之间的距离大概三五十米,就像梳梳子一样,每天在地里走,遇到遗址要进行记录。要知道走的都是农田啊,每天步行下来,双腿就跟灌了铅一样。调查都是每年的冬季进行,因为冬季地里边植被少,能见度比较高。把调查的内容一点点标注在地图上,再根据采集到的陶片,分成不同的文化和期段,这样就会形成若干幅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演变图。它能够清楚地反映从史前社会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向复杂的社会迈进,或者说,文明社会在一个区域怎么样一步一步起源,国家怎么样产生。我们现在说我们的国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有14亿人口,但是这个国家它最初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就是从区域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区域系统调查要发现和解决的问题。通过这些地图,你会明显地感觉到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遗址和人口突然增加,遗址分布非常多,有的地方比现在的村庄密度还要大,而且聚落分出了等级,出现了城。像尧王城遗址的面积有400万平方米,两城镇也有256万平方米,而且尧王城古国和两城镇古国之间,还有一个空间地带,一个边界地区。除了这两个大的城之外,还有像下边的二级、三级甚至四级聚落,它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最高统治者就住在城里面。张学海先生以城子崖遗址为中心,得出的“都·邑·聚”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在鲁东南表现得更为具体。像二、三级的聚落应该承担着行政职能。两城镇、尧王城两个古国之间的距离也就50公里左右。而且通过一、二级聚落串联,判断早在龙山时代鲁东南沿海交通线路已经形成,尤其是后来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从两城镇、尧王城往北、往南,直到黄岛、连云港,一级聚落数量更多,而且差不多都是45到50公里的距离。这就和文献里边的“万国”非常相似。《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是形容国家之多。文献还记载古国的范围也就是方百里、方七十里,基本上是人步行一天可以往返的路程。再大的话,要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王朝国家或王国阶段了,古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技术进步使得国家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夏禹的时候是“万国”,到了商汤时期,还有诸侯三千,到了武王灭商的时候,按照文献的记载,还有900多个国家。到了东周时期,山东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60多个有名有姓的小国,像邿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国,它的范围我想跟现在的一个县域差不多,甚至更小。这些小国家慢慢被吞并,形成春秋时期的春秋五霸,战国时期的战国七雄,最终由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庞大的秦帝国,并为汉王朝所承袭下来。所以我们的国家是不断地像滚雪球一样,从小到大,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发展而来的。王国阶段就是夏商周。秦国创始的郡县制国家治理架构,一直影响到现在。早期国家范围不大,而且就在许多区域实实在在地存在过。那我们就用双腿把它们寻找出来。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找寻国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文献上记载的或没有记载的,都要靠我们的双脚把它们找出来。看似笨拙,实际上很有效。所以,在家里躺在沙发上是搞不了考古的。这几十年的野外工作,我们取得的收获还是非常多的。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鲁东南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这是前13年的成果,获得了教育部当年唯一的考古类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的奖是很难评的,它每三年才评一次,评一次,考古只有一项。之所以获此殊荣,我想它的价值并不是说在于我们发现了成百上千的遗址,我们记录到的遗址是1400多处,调查覆盖的面积是1400平方公里,关键是证明了产生于其他地区的这种区域系统调查理论和方法,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它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且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对其合理性进行检验。当年我们项目组把调查的时间下限定在秦汉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已有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参考。或许当时对这一决定的意义没有十分地清晰,但事实证明历史文献,尤其是历史地理文献对于验证那些区域中心确实有参考价值。就在我们调查的覆盖范围之内,你可以轻易地找出来,哪些是郡,哪些是县,甚至秦汉时期可能存在的乡和里。可以说,我们在中国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大大丰富了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这是山大考古学科的贡献,当然也是中国考古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
我们一直在关注文明起源研究,国家也早已启动了文明探源工程,不过目前还是围绕着大遗址进行持续的发掘,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对大遗址的发掘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大遗址是聚落中心,而它所依托的基层社会,同样重要。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需要说的是,我们知道我国城镇化发展非常快,伴随而来的是遗址的破坏,而且在有些区域还是非常严重的,对它们的调查、记录,应该是越早越好。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就经常看到在修建的高速公路、铁路对遗址造成的破坏。因为这些修建或拓宽的道路,恰恰一般也是古代的交通要道,尽管考古工作者在道路修建之前要调查,甚至做些抢救性发掘,但有些遗址仍免不了要遭到破坏。这是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种紧迫性。
调查进展到第五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三个季度的发掘。发掘也是在聚落考古的理论指导下而展开的。两城镇的发掘,中美学者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使得这个项目的开展非常顺利。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开展,我觉得双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很重要。彼此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项目组非常清楚。比如发掘技术,对于西方考古人员来说,中国的土遗址是很难发掘的。我曾经参加过他们在墨西哥瓦哈卡谷地的发掘,因为古代的建筑都是石头建的,还是比较容易的,不会像我们这样“在土中找土”这么复杂。所以如果单纯由国外的学者搞,他肯定搞不了,必须要借助我们丰富的发掘经验。但是在分析检测、多学科交叉方面,毫无疑问欧美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所以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很快掌握了欧美的一些考古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当然我们还要结合实际,尤其是在中国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尝试这些理论方法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实际,并对其进行丰富完善。
当然,如果说没有和美国同行的合作,我们可能也会按照学科发展的规律,将考古学的重心转到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社会考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外合作使我们探索、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大考古学之所以能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和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转型有关系——我们比较早地开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比较早地关注到了环境考古、社会考古,获批了“环境与社会考古学科引智基地”“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比较早地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考古实验室。山大现在已建立起15个考古实验室,而且每一个实验室都有一些年轻的老师,他们大多是从海外学成归来,或者是送出国门进行访学交流归来的年轻学者。
 方辉教授参加了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国馆”的策展工作,这是他在馆内的留影。
方辉教授参加了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国馆”的策展工作,这是他在馆内的留影。
 2002年与费曼(中)、栾丰实(左一)在东海峪遗址
2002年与费曼(中)、栾丰实(左一)在东海峪遗址
现在的考古学越来越讲究实证的研究,关注社会发展、文明起源,以及人类所处的环境,人地之间的关系,人类如何利用资源、开发资源的研究。这些东西,光凭经验性的认知,光凭对器物的年代的认知已经完全不够了,必须要依靠发掘当中获取的过去不可想象的一些数据信息。比如看似最普通的土壤,里边就有很丰富的信息,然后采用科技的方法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比如当时的植被、环境、降水、生态、施肥等等。通过对人骨的研究,甚至能知道你吃过什么,知道你一生当中有没有经过迁徙。锶同位素就是研究人的迁徙问题的。这些东西都是考古学家自身无法回答的。你必须要找到你的合作伙伴。他们必须懂化学,懂同位素,懂环境,懂植物、动物,比如研究古代的酒遗存,要通过残留物分析,就是化学考古的方法。当然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比较细致,很少有学者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业来从事考古研究。不过现在情况也正在改变,因为我们自己培养了一些多学科背景的人才,这是一个趋势,会直接影响我们考古学科的发展。
多学科交叉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现在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和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了。考古学的转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开始算的话,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里边,有很多方面和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原创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跟踪,用他们的一些方法来分析我们的标本,在国内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最好。但是真正要领先,或者是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由“跟跑”到“领跑”,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个是应该要承认的。一个可能是在投入方面,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仪器设备虽然往往是不亚于他们的,但创新思维还是有所欠缺。创新思维最大的潜力是什么?就是多学科交叉,能否让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并攻关一些考古学问题。只有到了能提出问题并多学科交叉地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说我们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那么该怎样缩短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我觉得还是要从考古学问题出发。
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有这么多的实验室,你可以到山大的考古实验室里看看,无论是研究陶器、瓷器的,还是研究青铜器、铁器的,还是研究各种有机质的、无机质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实验室,找到我们相应的专家来给你分析、检测。所以关键还是提出问题,问题意识能够引导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
最近我关注的是在高等级墓葬里的遗物的产地问题。比如青铜器,早就有学者关注到了青铜器的出土地和生产地并非同一地点的问题。考古学界叫“示踪”,就是通过青铜器里所含元素,尤其是微量元素的分析,追踪其不同的产地。虽然在一个墓地里出土,但是它的来源可能各不一样,这就导致交叉学科冶金考古的方法创新。冶金考古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铜器的产地问题,包括铜料的产地,铜、锡、铅,以及那些微量的元素,可能各个矿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就有可能把它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在山东地区我们也开始在做这项工作,包括济南大辛庄遗址、刘家庄遗址,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些明显的来自于山东本地的矿源。
最近我自己更关注的是资源的控制和流通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和政治有关系,也和经济有关系。比如我最近写了几篇关于朱砂的问题。朱砂是我们日常大家都能看到的,它是一种矿物原料,是一种颜料。但是朱砂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颜料,它和道教炼丹术有关,有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实际上朱砂的文化含义并不是从道教起源的,它在史前时期就被作为一种战略物资,是北方上层统治阶层控制和使用的战略资源。丹砂的产地在中国非常有限,最好的产地,是在现在的贵州、湖南这一带。丹砂貌不惊人,但因为古人给它附加了很多的文化的含义,对它的研究就很有意思。古人在落葬时要用到朱砂,而北方又得不到,于是就要通过远途的贸易去获得。远途的贸易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为了丹砂的资源争夺,实际上古代发生了很多的战争。传说中帝尧和他的儿子丹朱之间的战争,体现的就是这一点。看似传说,实际上它也是历史文献所透露出来的上古时期存在的一个资源控制和反控制的问题。另外你像丹江,它的得名恐怕就和运丹有关。丹江是把南方的丹砂运往北方的一条必经通道,是沟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当然它不光运丹了,还把南方的各种各样的战略物资,包括铜和锡,往北方运。它也从北方往南方运盐等资源。
我们在北方发现了这么多的丹砂,它到底是哪儿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丹砂的汞同位素、硫同位素进行分析。拿它考古的标本和它产地的标本进行对比,现在初步的结论是支持我的这个看法的。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丹砂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区域是最好的,在秦岭里边,在陕西也有蕴藏,尽管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丹砂的开采可能比较晚,早不到史前时期。
有关丹砂的问题我是想说明,在现在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一些问题之后,你要想把它证实的话,光靠观察形态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靠科技考古来进行检测、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科技考古,要发展实验室来对大量标本进行检测、分析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丹砂后来的意义也变了。它一开始被用于殓葬,因为红色总是让人联想到血液,跟死后世界和相关信仰有关。后来古人用它来炼丹,古代炼丹家把各种各样的矿物放在一块儿,炼成所谓的仙丹。仙丹就是来自于丹砂,这就和道家的信仰有关了。再就是鎏金,鎏金技术也要用到丹砂,其方法就是古人所说的“汞剂法”。炼丹、制作鎏金器物,社会上供不应求,墓葬里边就不再使用这些东西了。所以它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为什么到了战国中期,墓底铺设丹砂现象突然就消失了?因为新的功能产生了。这是一种文化现象。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考古学家提出来,然后通过学科交叉研究予以解决。所以我想将来的研究肯定是朝这方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9·28”重要讲话里提出来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万物都有一个源头,这源头往往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或者记载出现得比较晚,实际上古人早就在使用了,这就需要考古来解决。包括我们的小米的栽培、大米的栽培、小麦的引入等等,这些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就需要植物考古来解决。你说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四大发明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粮食。大米、小米的栽培,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而且都有1万年左右的历史。当然同样,我们也吸收外来的因素,像小麦、大麦,是从中亚、西亚传播到中国的。另外还有大豆、高粱、蔬菜瓜果等等,都有一个从野生到栽培的过程,动物也是如此,马、牛、猪、羊、鸡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靠动物考古学家通过对地下出土的遗物进行大量检测、分析,才能搞明白它们从野生到驯养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多学科交叉,强调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对遗址出土的古代遗物进行分析检测,拿出实证性的成果。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另外在专业人才培养上面,我们也在探索一些新的路子。今年我们山东大学开启了“考古+拔尖人才培养2.0”升级版计划。就是每年在新入学的本科生中,选拔20个左右学生进行本硕博一贯制的培养。我们的想法是从本科生阶段就要打好基础,历史的、考古的基础,然后进行多学科交叉的培养,到硕士、博士阶段,让同学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有自己的主攻方向,然后做最好的研究。我们把这个班命名为吴金鼎班,也是为了纪念吴金鼎先生。他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命名者,也是山东大学、同样也是山东省考古学科奠基人。希望“考古+拔尖人才培养2.0”升级版模式,能够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走出我们的一条路子。
 方辉
方辉
考古总会给人以期待。在进行一次调查、发掘前,你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也许几天走下来,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也许发掘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也没有什么重要收获,但是它总是给你以期望。实际上,没有发现也是一种发现,也不止一种结果和回报。考古学它能让你永远充满期待,充满探索的欲望,这是这个学科的魅力所在。
 方辉
方辉
考古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在中国也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的学科,不断地把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知识容纳进来。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的历史,但它采用的方法很多又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以也有人说考古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有人说,考古学需要得到人类学的验证(在北美,确确实实考古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人类学)。这当然都有它的道理,因为考古学通过古代的遗存研究人类的行为,这和人类学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有时你很难给考古学一个明确定位。实际上,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它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把相关领域的知识融合进来,所以它永远是一个开放、包容、青春永驻的学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