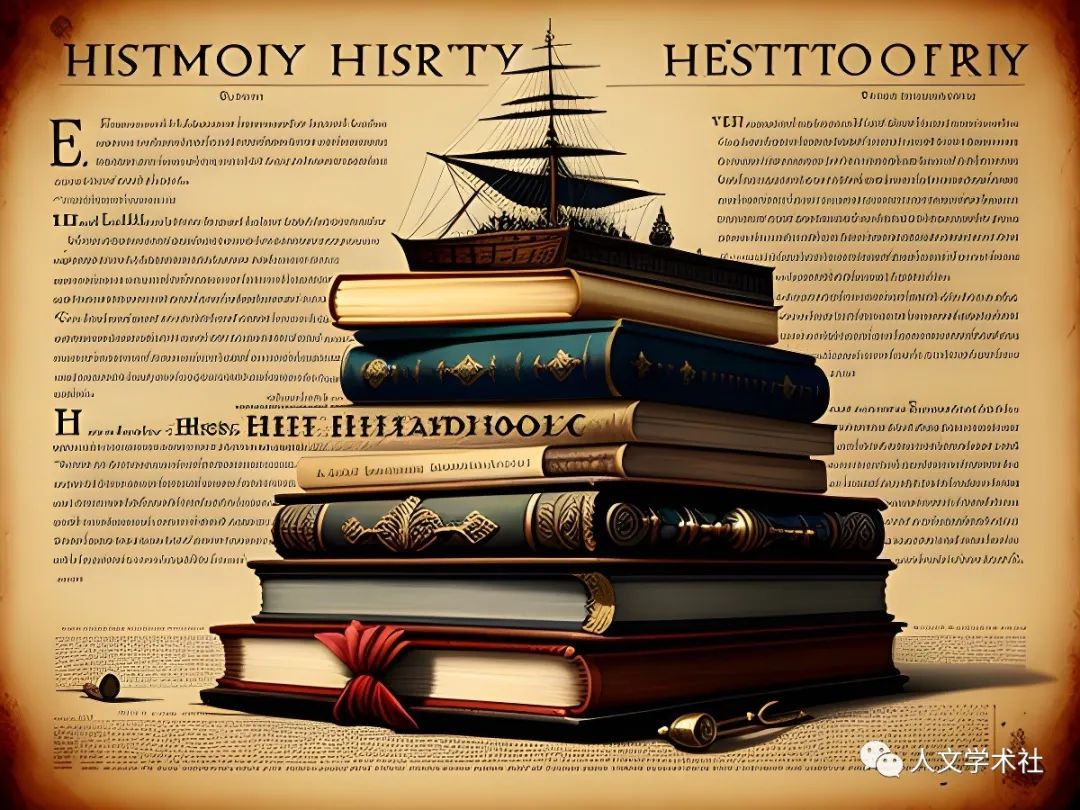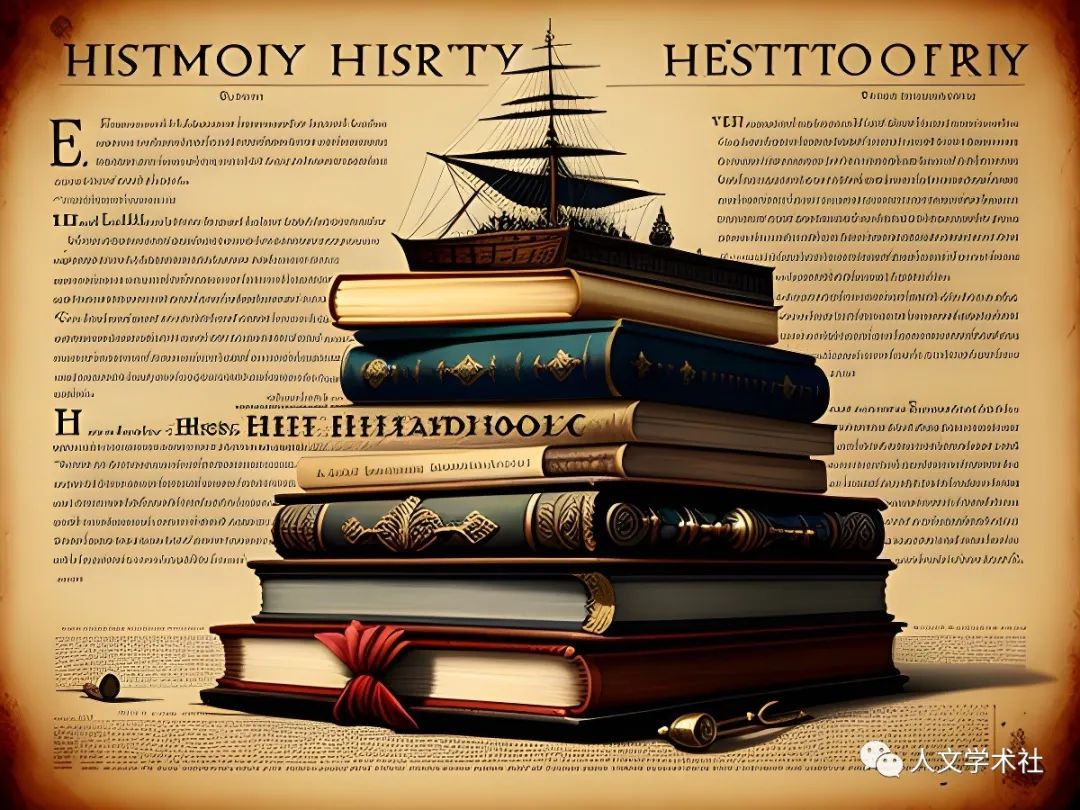论历史学票友的基本修养
字号:T|T
2023-09-11 16:49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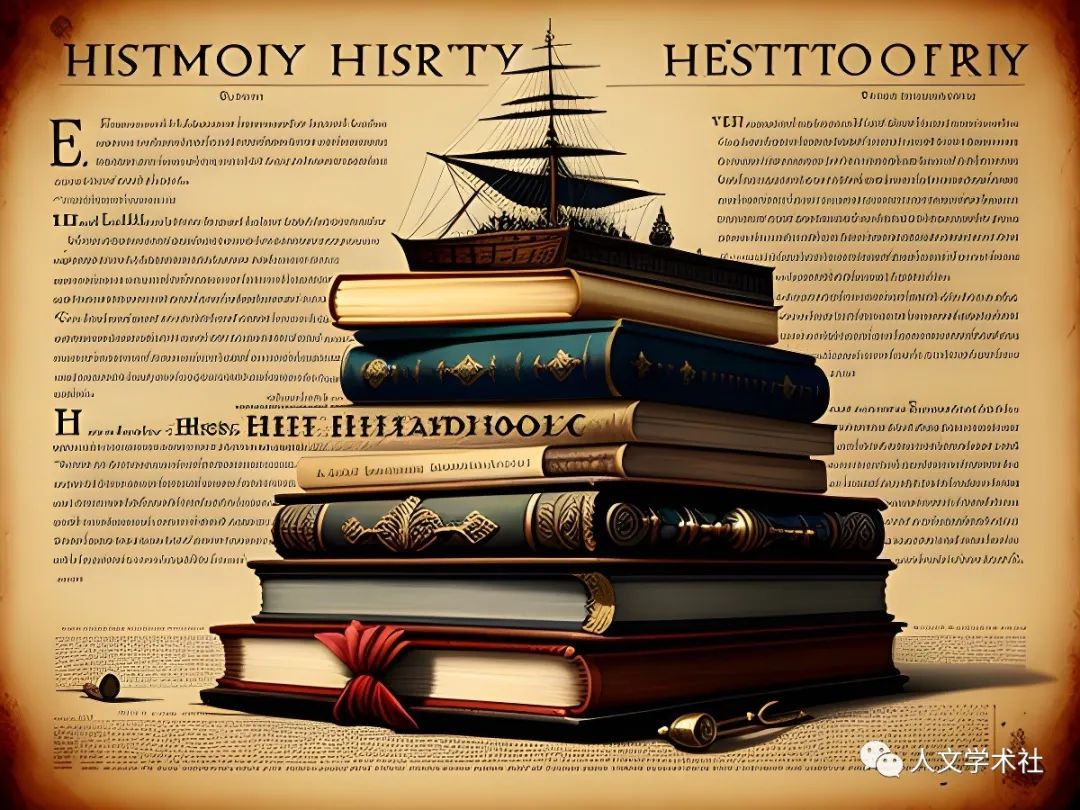
论票友的基本修养
碎瓦
上半年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著名学者马俊亚在会上做主题发言时,自称为“历史学的票友”。如此谦冲自牧自然是令人仰止的,但我却实在不能接受。因为像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历史从业人员,向来以“票友”自居,游戏畛域,即使做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也好以这个身份遮蔽才质的庸碌。想起初进馆时,听老前辈谆谆教导:我们这一行啊搞历史,达不到人家那个专业水准,顶多就是个票友——深以为然。如今大佬非要坐这个位置上,那咱可不就是无地自容了。
在众多人文学科里,历史学是最要求严谨论证的学科,讲究以原材料为中心(source-oriented),“句句有出处”,连缀史料导出的观点要有严密的逻辑链支撑。就像考古挖出些文物碎片,先要确凿其质地和年代,再慢慢拼凑出文物本来的样子,这个拼凑的过程绝不是无端之想象,要参考既有类似样本的模样,要反复验证实际上的合理性。所以有人把研究历史问题比喻成推理破案、寻找真相的过程,有客观的真实要求,也就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史学之难,难在虽可单列一科,但与各人文科学之间暗通款曲,交织复杂,治史者需见得其点线面体,方可把握史实的基本面貌。真正有志于钻研历史的学者,要有大把的时间埋首于故纸堆,要“专精”也要“博通”,非坐得数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不可。故而常有人说,历史是老人家的学问,“青年史学家”的头衔固然常见,但能真正戴稳的却寥寥无几。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到互联网时代,如今亦要有强大的资料收集和信息检索能力,梯山航海,彼岸漫漫,怕是多少历史学人必经的心路历程。
此外,历史还是个非常烧钱的东西。一般的资料,靠图书馆和网络资源可以解决大部,但终归还是要买一些难找的书,或去淘一淘古籍、逛一逛孔网,或者求助于电子书贩。珍稀的史料,如年代久远的名人信笺、品相良好的民国图书,轻易就成千上万;就算是免费公布的档案,第一时间就争取到差旅机会和路费跑去查阅,也不是人人都有的能力。90年代苏联解体后,“以商养学”的沈志华教授靠黄金生意赚的钱,跑去换来了上万份珍贵档案并编选出版,为冷战史别开生面。沈教授的治学精神我们或许是可以学一学的,但这挣钱的本事,大部分学者如何学得?
文化事业单位比如史志办、地方史办、党史办,大型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史料,倘若起了兴趣想要做点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的学术成绩,离不开南京博物院的丰富资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吴元丰是清代满文文书的专家,看满文档案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著名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有过上海文史研究馆的经历,北京大学的王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职。大陆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先生在二史馆查阅资料时,原本的课题是北伐战争,但他偶然发现一份并不在调阅单的资料,竟打开了学术的新门,这份资料就是蒋介石秘书毛思诚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类抄》。从此以后,杨先生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接触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大溪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地所藏档案,为其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对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的上班族来说,一旦钻研起学术,就会发现时间上捉襟见肘,精力上疲于应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身份是票友,成果聊以自慰,做得好一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也仅仅是注意而已。拿咱档案人来说,借接触第一手史料之便,八九十年代也曾站到历史研究的前沿,但随着学科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就落后了。票友们搞研究,优势在于背靠大树好乘凉,劣势也是容易只见这棵大树,不见森林。因为票友们的问题意识,往往肇发于手头处理的一批材料,组织文章时首先在通史、熟见档案中补缀,再引注一些相对好找的资料,大体便成形了,再修改增删多是章句枝节。如此一来,其实在史料的丰富程度和对比特性上,不但不强于一般的学者论文,甚至要逊色不少。因为随着网络资源的开放和风气的提倡,学界普遍提倡使用多方、多语种的史料引证,以显视角多样,格局打开。但常年身处体制单位的人,学养单一、目力狭促,做学术往往不够专业严谨,有时候还要闹笑话。
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著文为档案去魅,如桑兵教授认为“尘封的档案不可能完全掩盖历史的真相”,档案与其他记载抵牾而档案未必正确的情形经常出现,诚如斯言。档案人不仅对档案失实的情形有所体会,还苦于档案的价值和有效性参差不齐。因为说白了,档案多是旧时的文牍,自古以来文牍都充斥着官话、套话和废话——等因奉此之乎者也,还因年代久远而带来各种污损卷折、褪色洇染,基础的辨识就耗去大量精力,枯燥的感受在所难免,再鼓动起心思去做学术,并非一件易事。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档案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关键在于如何去利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介绍了他的资料来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巴黎和几个省政府的档案,并对此评价道: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和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
这句话就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档案的“初衷”限制其使用。档案作为官方文件被制作出来,其原始的制作目的可能与后人的研究目的圆凿方枘,存在大量的“隐藏信息”可供发掘。学者可通过多种方式来利用,例如将某一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来定量分析。余新忠先生在《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里,通过折线统计图分别展示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瘟疫的关系,是为一剑走偏锋的典型案例;黄宗智先生借助满铁档案分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和商品化特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到共性主题的档案去“讲故事”,尽可能丰富某一事件的细节,国外学者似乎用的更普遍些。如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茨堡的名作《夜间的战斗》,就是从看似荒诞不经的宗教法庭审判档案中采撷信息,深度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的社会史和心灵史。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有这种尝试,近年来比较出圈的作品,罗新《漫长的余生》和鲁西奇的《喜》也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占有史料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学人的必修课,如今虽然依旧不可或缺,但事情却在发生变化。互联网时代之前,无论何种性质的史料都要实实在在拿在手里才叫占有;现在有了互联网,似乎资料存进硬盘、网盘就为我所用,其实大不然。笔者在网上加过一些“史料分享群”,许多人对电子史料孜孜以求,竭力包揽,就希望写文章时博作参考,方便引用。这算作一种“赛博治学”,好是好的,但若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却不注意历史资料的有效性与适用限度就是舍本求末了。史料如海,“搜罗备用”其实不如“用时搜罗”,把精力集中在思考问题上可能会更有助益。
再说史料固然重要,怎么用史料同样重要,做论文的功夫到底不在史料养分的堆砌,而在于对史料的处理。参加过多次研讨会后,笔者见识了一些尚不完善的论文,其中不乏史料丰富但处理欠缺章法的类型,就产生一种浪费。严耕望在《治史三书》里强调,新史料极其难得,可遇不可求,这时就要退而求其次——“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这当然是高明的研究者才能做到的,但普通人也可学习这种精神。譬如A关于某事有些许评论,B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都三三两两、不成系统,你正好了解这方面的史料,那么综合处理一下,就可能会有更中肯的看法,或者能在前人的认识上进一跬步。
钱穆有云,学术上有成就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和傻气,天资不高反而有可长进的空间。所以说票友们虽然比不上专业学者,但也并非没有一较短长的机会。我们的优势在于日常接触档案,不愁史料枯竭,关键是要从旧档案里看出新东西来,这是作为历史学票友的一个基本修养。如果日常浏览档案时心如止水、思不出位,自然提不出问题、拿不出观点,可谓背靠金山却沿街托钵,那就离学术研究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