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复原研究
字号:T|T
2023-08-16 08:44 来源:南方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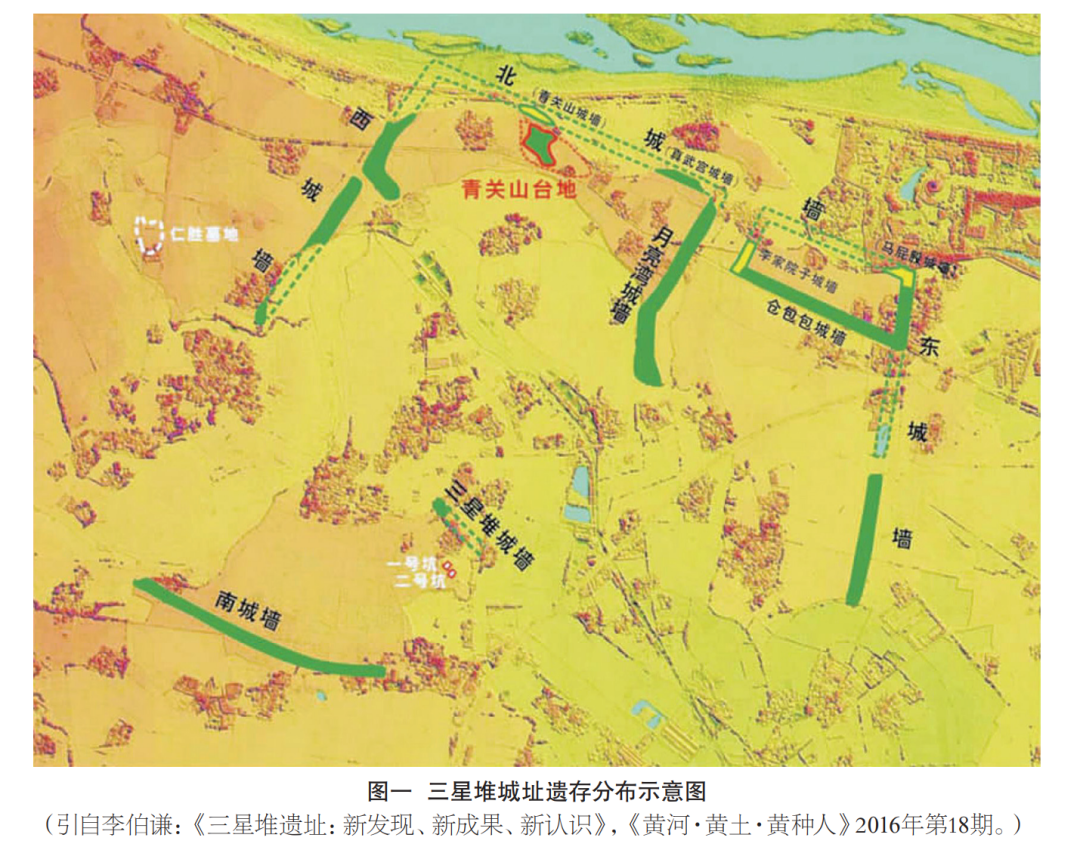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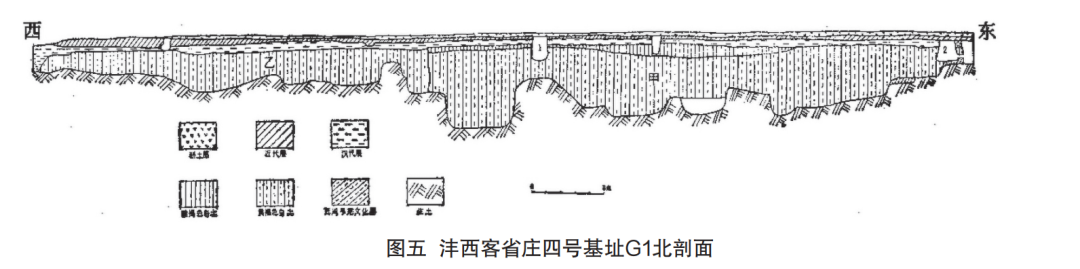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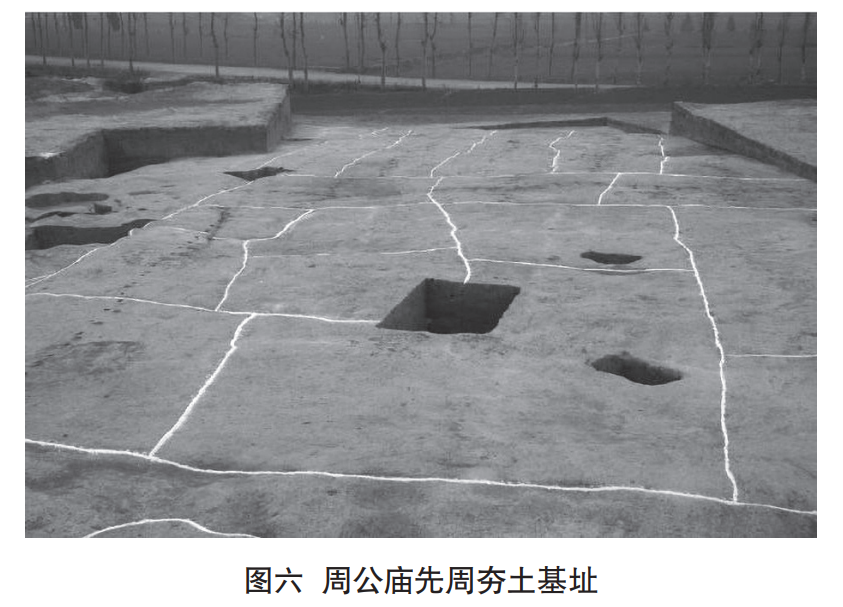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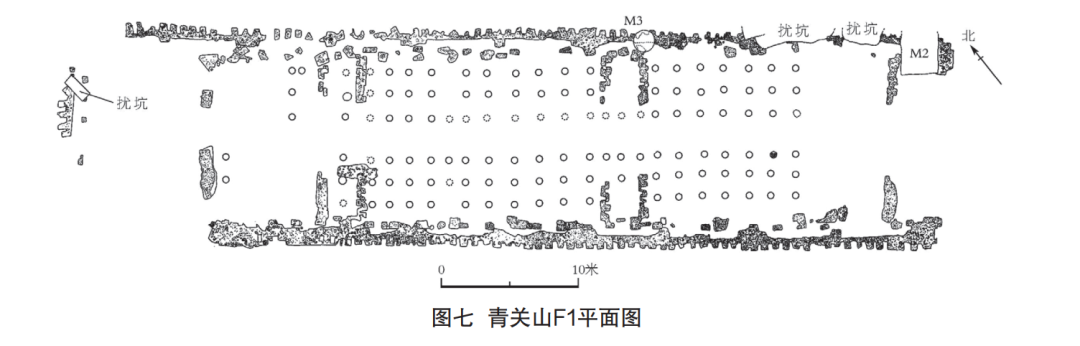



[1]雷雨:《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前的一朵奇葩》,《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2月8日A12版。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7、37页。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