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564场考古报告,我看到了什么
你在哪个地层?
10月23日8点15分,西安。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前十五分钟,
走进陕西宾馆的千人会议厅,
大家的内心OS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排旧石器考古,
第二排新石器考古,
第三排夏商考古、秦汉考古,
第四排两周考古、三国至隋唐考古,
宋辽金元明清考古在第五排……
过道上,工作人员举着蓝色的“地层标识”牌牌,
你属于哪里,一目了然。
作为媒体,自然坐在现代“耕土层”上。


这是一个什么大会?
用新闻体的表达:作为中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规格最高的国际性高端学术会议,中国考古学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促进中国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为推动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开幕回顾)。
中国考古学大会已经举办了三届,今年是第四届,在西安。受中国考古学会的邀请,作为唯一的浙江媒体,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大会。上一届在河南三门峡,很特别,“百年一会”,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而这一届,是一个起点,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所说,是中国考古学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第一次大会。
每一届大会,都会聚焦一个特定的重大学术前沿问题,这次的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正经的新闻体播报完了,如果用非新闻体(歪楼体)表达:和近千位考古学家一起开了三天会,是种什么体验?
(一)
除了近千位考古学家这个数字外(实际数字是800多位),还有几个数字:他们参加了27个专业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开幕式上座位表上的“地层”,就是其中几个专业委员会,你可以理解为中国考古学各分支领域。
而上一届大会的数字,是23个,本届新增了4个专业委员会:考古遗产、陵墓考古、长城考古、大运河考古与保护等领域,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这两年考古学学术研究中的热点。
这三天,27个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564场报告,共收到论文568篇——参加单位、参会代表、收到论文,创了历届新高。
每天,我都会经过这张迷路星人会议室指路牌,你要去哪个房间听小组讨论,得先在茫茫人海中找对房间。来的晚了,可能没位子,比如“新石器考古”小组的房间总是挤到门口,去晚了就只有墙边站站——站着听也很好。


“新石器考古”专委会讨论现场 图片来自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
“张老师刘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陈老师……”几次开会前十五分钟,进电梯,会先叫上一遍。“你后面还有一个老师。”转头,又补叫。大部分不认识+社恐如我夹在里面,默默偷听。“都是老熟人。”大家都笑了。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又一次进电梯,大家只叫同一个老师。穿着碎花上衣,优雅的安老师跟每个人点头,你好,你们好。安老师,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之女。
偶遇星星,也是大会的重要课题。比如第三天,夜幕中的宝鸡周原博物院,偶遇了等在门口的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他从杭州“回周原”。
又一次吃饭前坐电梯,这回只有两个人。“最近挖了啥?”“我最长的墓坑5.5-6米多。”“这么长。”
每次吃饭,人多,大家在各种大圆桌前“捡漏”坐下。
“我看您面熟,您去过南阳黄山遗址吧。”“经常去呀!”“你现在在哪儿发掘?”“在郑州。”一边啃泡馍,一边加微信。这是考古学家之间的打招呼方式。(二)
564场报告中,有一场“长安论坛”在开幕当晚7点半举行,不限专业小组,大家都可以来听,主题是石峁遗址的考古和研究。
石峁是陕西考古明星班里的一位大明星。
大家都知道,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强省,44年前,中国考古学会就是在西安成立的。我们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一楼展厅里,可以看到一张学会成立的老照片,看看卡司:夏鼐任理事长,裴文中、尹达、苏秉琦任副理事长,王仲殊为副秘书长,陈滋德、安志敏、宿白等8人为常务理事。温州人夏鼐在大会上作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报告。

2021年,陕西建成了全国首家院馆一体考古机构,全国第一家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开了国内考古机构改革之先河,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发展提供了“陕西方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第一天的主题发言中说,以陕西考古研究院为例,陕西近年来发现涉及上到旧石器、下至明清古代遗存数百处,出土文物10余万件。
如果用前几天的热搜体来说,#西安大学生宿舍楼下就是考古现场#(当然表达是有问题的)。用网络流行语来说:看不完,真的看不完。最后一天,各地考古学家分批次参观陕西考古博物馆、周原遗址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回来忍不住发圈:“陕西考古太厉害了,而且‘陕西考古博物馆’,是迄今为止我学习参观过的全国最好的博物馆,没有之一。”外地兄弟同行留下了羡慕的泪水——“随手一发都是宝——家大业大,实干用心,我辈楷模。

太喜欢这块地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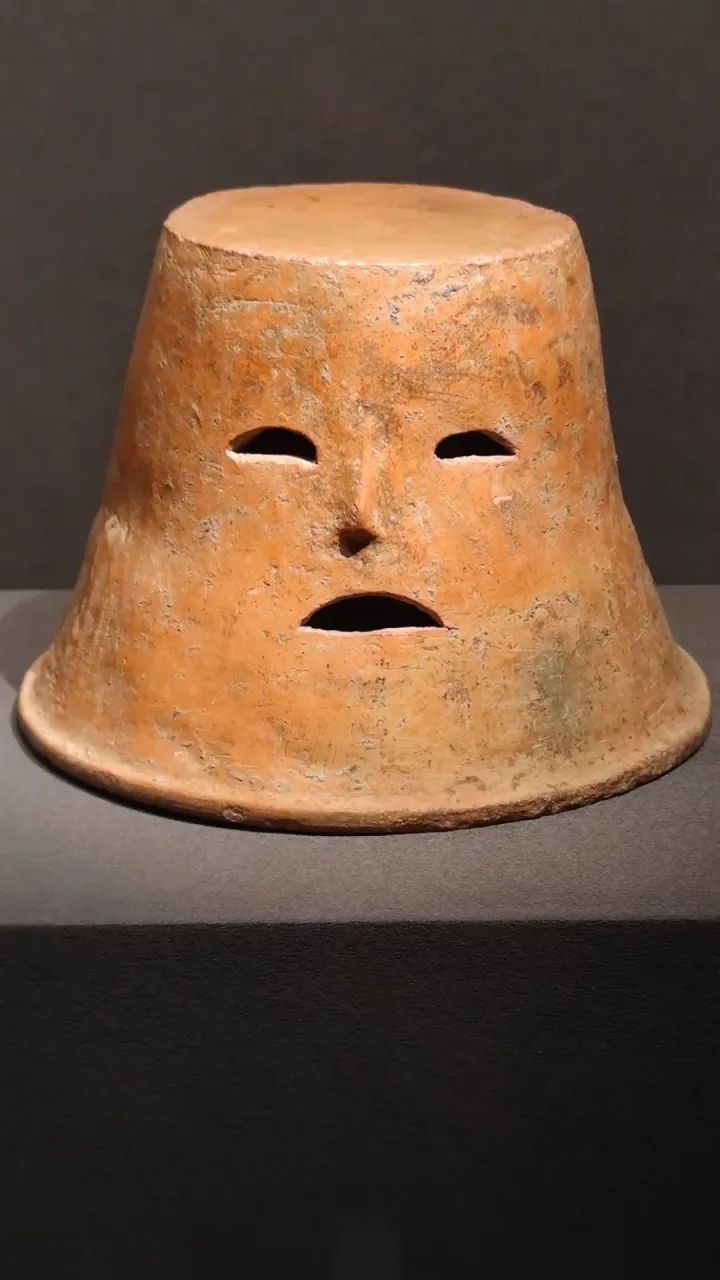
目瞪口呆体

真的放不下了
扯远了,回来讲“长安论坛”的男主角“石峁”——2012年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020年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21年入选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先来一个知识条:
石峁遗址在陕西省神木市石峁村,地处黄河西岸、黄土高原北端,主要遗存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这是一个石头城,也是东亚地区所见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石峁东门址和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早期阶段。
2011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发现了它的三重结构——皇城台、内城、外城构成,城内密布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城外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城门、城垣及大型建筑均由石头包砌,防御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从2022年发掘至今,皇城台共发现墓葬40多座,墓葬成排分布,并用石墙划分茔园,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今年还新发现两处通道,将墓地区和大台基区域有效连接。一条为下陷式道路;另一条疑似地上通道,由台阶和平坦的地面结合而成,位置恰好处于皇城台的中轴线上。
论坛开始前,考古学家们已经进行了一天的小组讨论。晚上7点半,一进门,又一次“被逼墙角”——晚上的报告居然那么多人,大家感叹。后排、过道,不断加座,加到加不了,直接贴墙站。

“同志们抓紧就坐,赶紧把位子占了。”开始前两分钟,主持人也忍不住提醒。
对谈环节,北京大学教授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张弛、浙江大学教授刘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大咖们都到了现场,大家的问题也很多。石峁是否和良渚一样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比如这个观众提问,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做了一点课堂笔记——
赵辉:什么是国家?有一个本质,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公共权力,表现在对内对外合法使用武力,至于有没有城、金属、文字,这是权力的外在表现,良渚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是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早期文明。
石峁如果和良渚去比,我觉得差不太多,它不是在良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多线条发展,用古DNA的结果(注:最新通过古基因组研究分析,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起源),石峁是在本土文化的传统上形成,自己发展起来的,大家不约而同往文明化方向去走。
但从国家的本质形态来说,石峁有个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还表现在唯我独尊。石峁这个大城出来以后,其他在规模上都是一种从属的状态,不是和石峁并驾齐驱。建设如此大的工程,发展手工业,远距离的贸易,都是文明化程度的表现,综合起来确实有这样一种国家的结构。
李新伟:还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石峁,大家都很震撼,但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石峁的发展,城圈成一圈,像一个大羊圈一样;把玉器插入石墙,难道石峁人不会用这个玉器吗,像暴发户一样随便插进去(注:“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很特殊的现象。在城墙修建过程中,石峁人将玉牙璋、玉钺、玉刀、玉铲等嵌入墙体或埋入墙根)现在,我们对石峁已经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改变了很多看法,没有人能否认石峁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又一次让我们认识到文明形成宏大的进程,要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在石峁之前的1000多年,5000年前,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看到各地灿烂的发展形成了苏秉琦先生说的“古国”的社会,满天星斗,与它们同时发展的,是各地区的文明交流密切加强,大家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就是后来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也可以说是“最初的中国”。第一个灿烂的结晶就是良渚文化,完成了一个早期国家的发展,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在良渚形成的时候,东部其他地区城邦林立,还没有达到良渚的发展程度,但都在发展。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属于仰韶文化的范围,处于一个动荡整合的阶段,仰韶的一批先民往西迁移,一直到甘肃西部,深入到河西走廊,给我们的文明开辟了一个重要空间,黄土高原的文化和新空间的开拓,良渚的发展,都为后来石峁的发展奠定了伏笔。
我认为前面两个伏笔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良渚文化衰落了,但那个时代形成的主题,也就是良渚形成的宗教观念,构建国家的一些方式,广泛影响了龙山时代的发展。江汉地区,山东地区,都发现了良渚风格的玉器,都受到了良渚的影响,看到了对良渚宗教观念的接受,这也传到了黄土高原地区。包括石峁的一些皇城台的雕刻,可以清晰看到良渚的影响。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仰韶先民开拓了西部空间,引进了西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牛和羊的引进,当然也有金属和小麦,但没有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牛和羊极大改善了黄土高原人的生活,我们看到了石峁的显著发展,黄土高原也形成了发展。
说到牛和羊,张弛也提到了石峁人“半农半牧”的新型农业经济——
张弛:说石峁,第一点,就西亚、中国和美洲三大农业原生地的情况来看,在农业起源开始后,只需要四五千年,社会迅速复杂化,开始出现复杂社会,用西方的新进化论来解释,就是先进入“酋邦”阶段,再发展成国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是,陕北并没有,一直是迟迟的,甚至河套地区有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发展了上千年,社会并没有复杂化,到仰韶晚期反而有些退化,农业并不很发达,采集狩猎反而比较发达。但是从仰韶晚期之后,从采集狩猎、农业不怎么发达的社会,短短几百年内,发展成了另一种新型文化,石峁,就是这种新型文化的一个结晶,是最高的代表。
这种新型文化,我个人认为,是在旱作农业的基础上,养了西方溜达过来的那些山羊、绵阳、黄牛,在这里产生了畜牧业,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半农半牧的新型农业经济,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要不然,光种那些小米,陕北要养活那么多人,没有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的支持,靠着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旱作,只种两种小米,只养一种猪,我估计做不到。但是,恰恰在仰韶晚期之后,出现了一种契机,新型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首先在陕北地区,继而在整个黄土高原发展起来,石峁的出现,跟经济基础有关。
第二点,我们都被石峁的宏大的聚落形式震撼,这种聚落形态,也不是仰韶以来传统的,而是和经济发生变化几乎同时期发生,这种新型的聚落形态,我称之为窑洞式的聚落。而在此之前,仰韶都是半地穴的房子,只能在平地上沿着河谷阶地分布盖房子,大多数都是围着一个环壕,里面有大房子、小房子,背向聚落的中心。
出现窑洞式的聚落,是仰韶文化衰落之后的结果,人们都住在小窑洞里了,越来越深入黄土高原的腹地。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就产生在山坡上修窑洞,山顶上修高等级建筑的聚落模式,只是在这种聚落模式当中,石峁的高等级建筑修得格外高大。这也是新型的经济在聚落景观上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第三个,再说一下社会。很多人在问,石峁是不是国家?在考古上,想“发现”一个国家,是要找到证据的。能不能挖到王墓,要做大面积的揭露,很难,也很难一下子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就石峁现在的情况,我们看石峁的结构,中间的皇城台我叫它“城中城”结构(与良渚古城的中心宫殿区莫角山是一样的社会景观),皇城台的的城门和东门址的城门一模一样,即便东门址是后来扩建的,内城的城门,也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内城和皇城台一起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石峁的城门极具防卫特征,要拐好多弯。也就是说,石峁这个城,不光要防外人,防邻居,内部的人,也要防,我管它叫城中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即便在城内,也很紧张,还要防自己人,就这个聚落景观来说,社会分化方面,石峁体现得特别极端,更何况,皇城台上住大建筑的人,跟住小窑洞的人,社会差别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现在能发现的大量的玉器、青铜器、海贝、骨针,都发现在皇城台往下倒的垃圾里,住在皇城台上的人,有非常大的能力获得远道而来的资源,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要拿证据来说话。
在第二天“新石器考古”专委会的讨论中,方向明也提到了张弛的观点,顺便剧透了即将开幕的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大展。
方向明:河姆渡遗址发现后,严文明先生在《稻作农业和东方文明》的文章中讲到,“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体系的紧密结合与充分发展,才出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古代东方文明。”对于中国文明的第一波起源,这个结论依然经典。不过听完“长安论坛”,我觉得,恐怕还有第二波文明起源的讨论余地,我比较同意张弛老师说的以石峁为代表的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和之前的旱地农业系统完全是两码事情,这种经济模式恐怕是催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
有观众问:石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研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种独特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归纳石峁模式?
陈星灿:石峁的发现基本上在2011年以来,发现之后才纳入探源工程的研究范围内,是我们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尤其在400毫米降水线北方长城地带,有这样一个巨大的石城,周边也有相当多的石城,比如碧村(注:据不完全统计,石峁遗址附近有不下10处石城聚落。这些聚落奠定了“石峁王权国家”的社会基础),规模小一点,但结构类似。表明4000年前后,在长城沿线一带,已经产生了国家,已经产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它对我们了解这个地区的文明起源,国家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考古学家把这个地方文明的起源称为北方模式,虽然不是大家都能接受,但体现了不一样的特点。包括以石头为材料垒筑这么大的公共工程,虽然还没有发现王墓,或者是还不知道,我们发现的墓葬都盗掘了,最大的那个还没有发现,但是从其他方面,从公共工程的巨大,专业手工业的存在,劳工力投入的巨大,远程贸易等,可以很明确知道在北方地区,是最大规模的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国家,但我们不知道范围多大,这对我们了解中华文明5000年发展相当重要,对我们了解北方地区的文明起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